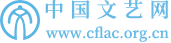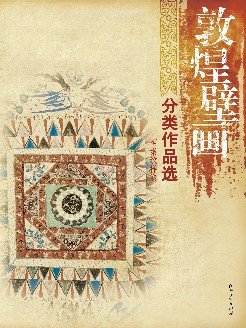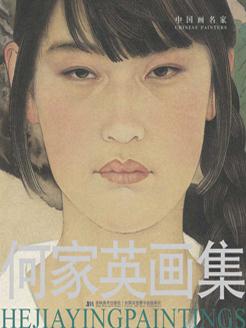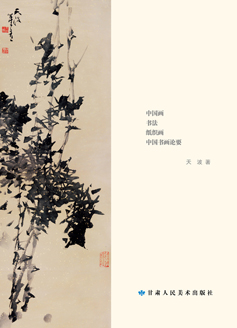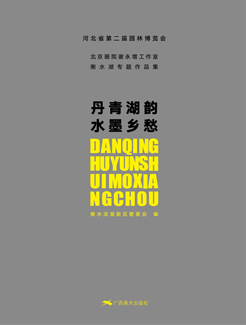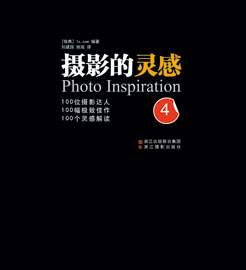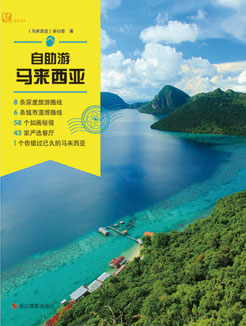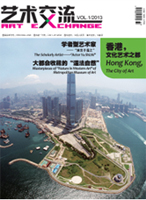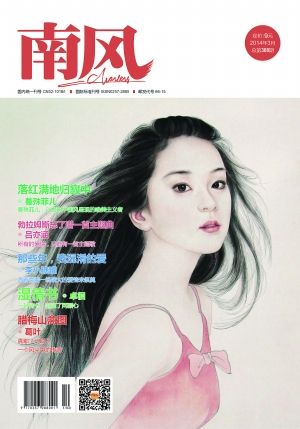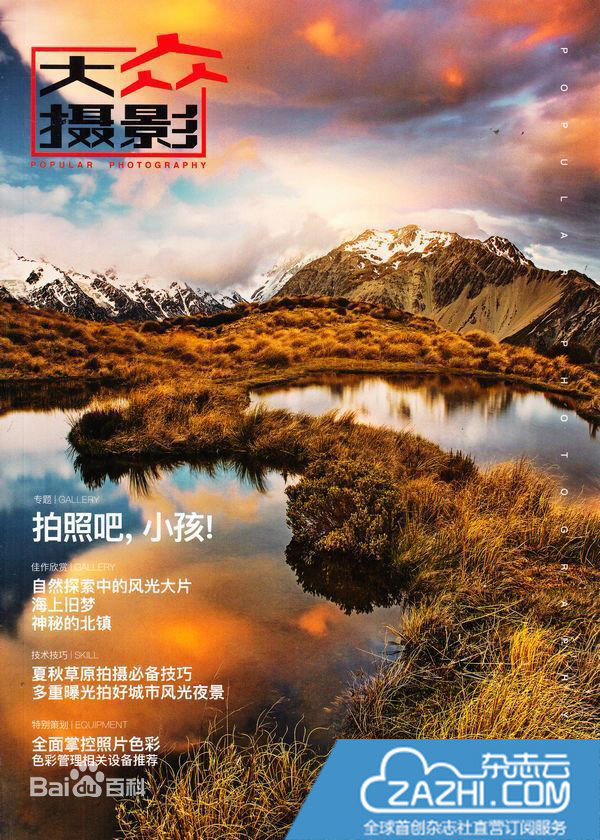但凡學(xué)術(shù)研究總有一個(gè)漫長(zhǎng)的論證過(guò)程,考古學(xué)當(dāng)然也不例外,從它的勘探、發(fā)掘到最終得出結(jié)論,無(wú)不需要經(jīng)歷一番詳細(xì)、周密的考量。然而,在這個(gè)信息爆炸的年代,當(dāng)考古遭遇了傳媒,本該慢工出細(xì)活的考古也變得有些心急火燎,往往是八字還沒(méi)一撇,就已經(jīng)在各大傳媒、網(wǎng)站上炒得火熱,而如此急慌慌的結(jié)果,常常是事與愿違,最終淪為考古學(xué)界的笑話(huà)。
河南孟津“李煜墓”的“流產(chǎn)”便是這樣一個(gè)匆忙撩開(kāi)面紗的學(xué)術(shù)笑話(huà)。話(huà)說(shuō)前些日子,河南省孟津縣文物局爆出猛料:當(dāng)?shù)匕l(fā)現(xiàn)了南唐后主李煜的墓葬。一時(shí)間,“河南孟津李煜墓”幾個(gè)字幾乎聚焦了全國(guó)考古人士的目光。然而,這樣的消息傳來(lái)才沒(méi)幾天,澄清的話(huà)便接踵而至:該消息發(fā)布屬于工作人員疏忽所致,“李煜墓”目前并無(wú)考古學(xué)上的依據(jù)。這可真是“來(lái)也匆匆,去也匆匆”, 來(lái)去匆匆間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所謂李煜墓不過(guò)是當(dāng)?shù)氐囊粠樵福o(wú)多少科學(xué)依據(jù),而真正的李煜墓在哪兒其實(shí)誰(shuí)也說(shuō)不清楚。
是考古者的倉(cāng)促爆料,還是傳媒人急于吸引眼球的刻意炒作?細(xì)細(xì)想來(lái),一個(gè)縝密的考古結(jié)論理應(yīng)建立在一套擁有多個(gè)步驟的考古流程以及一條非常完整的證據(jù)鏈的基礎(chǔ)之上,僅憑當(dāng)?shù)匚奈锞值囊淮巫咴L(fǎng)調(diào)查如何能夠拿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證據(jù)?然而,處在信息飛速傳遞的當(dāng)下,人們似乎已經(jīng)容不得靜下心來(lái)進(jìn)行科學(xué)的論證與商榷,而更傾向于把猜測(cè)當(dāng)事實(shí)來(lái)吸引眼球了。
誠(chéng)然,我們身處在一個(gè)崇尚“快餐文化”的時(shí)代,但考古學(xué)畢竟是一門(mén)嚴(yán)肅的科學(xué),考古發(fā)掘需要靜下心來(lái),長(zhǎng)年累月地田野作業(yè),容不得半點(diǎn)心浮氣躁;考古結(jié)論也只能而且必須建立在已有的證據(jù)之上,不可有絲毫的憑空猜想。猶記前些年,河北磁縣灣漳村曾發(fā)掘出一個(gè)高等級(jí)壁畫(huà)墓,盡管考古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該壁畫(huà)墓極有可能是一位北齊皇帝的墓葬,相關(guān)出土材料也很豐富,但終因各方面證據(jù)不足,考古界目前也僅能以“灣漳大墓”稱(chēng)之。——這才是科學(xué),一份材料說(shuō)一份話(huà)。
如果說(shuō)考古研究講究的是縝密思考、科學(xué)論證,信息傳遞追求的則是抓人眼球、先聲奪人,兩相碰撞,一旦考古者敵不過(guò)聚焦在鎂光燈下的誘惑,難免就會(huì)造成考古結(jié)論被催生、早產(chǎn)甚至流產(chǎn)、夭折的命運(yùn)。
這不,這邊“李煜墓”才剛剛淡出人們的視野,那邊“發(fā)現(xiàn)比甲骨文還早1000年的中國(guó)最早文字”的消息就已經(jīng)勁爆而出。事件緣起于近日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的一次考古,考古人員發(fā)現(xiàn)出土的器物上有大量的刻畫(huà)符號(hào)。相關(guān)結(jié)論還在論證之中,媒體就已經(jīng)搶先報(bào)道,并稱(chēng)其為“中國(guó)最早的原始文字”。眾所周知,甲骨文距今才3300多年,相比蘇美爾和古埃及的文字晚了約2000年。
作為文明古國(guó)的后代,聽(tīng)說(shuō)發(fā)掘出五六千年前的文字,將中國(guó)最早擁有文字的歷史一下子提前了1000多年,幾可與蘇美爾、古埃及文字分庭抗禮,在感情上比較興奮是可以理解的,但學(xué)術(shù)畢竟是學(xué)術(shù),需要有超越狹隘感情的理性和客觀(guān)。事實(shí)上,在古陶器、古巖畫(huà)上發(fā)現(xiàn)早于甲骨文的先民刻畫(huà)的符號(hào),對(duì)我國(guó)考古史而言并非什么新鮮事:上世紀(jì)30年代,考古學(xué)家就曾在裴李崗文化到商代前期的器物上,發(fā)現(xiàn)了許多與商周甲骨金文構(gòu)形相似的刻畫(huà)符號(hào);1952年,又在陜西西安半坡村發(fā)現(xiàn)了距今6000年的陶器上的30個(gè)刻畫(huà)符號(hào)。此后,類(lèi)似的符號(hào)不斷被發(fā)現(xiàn)。2009年,考古學(xué)家在陜西延安黃龍的新石器遺址中意外發(fā)現(xiàn)了一塊帶有刻畫(huà)符號(hào)的陶器殘片,共有12個(gè)燒制前刻好的符號(hào),筆畫(huà)酷似現(xiàn)今的英文字母或羅馬數(shù)字符號(hào)。
如果套用媒體的說(shuō)法,在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發(fā)現(xiàn)的刻畫(huà)符號(hào)即為“中國(guó)最早的原始文字”,那么,上述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有的甚至比該刻畫(huà)符號(hào)出現(xiàn)的時(shí)間更早,為什么也都沒(méi)有推翻甲骨文的地位?理由很簡(jiǎn)單,對(duì)于類(lèi)似的刻畫(huà)符號(hào),盡管郭沫若曾明確表示“可以肯定地說(shuō)這就是中國(guó)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guó)原始文字的孑遺”,但它們究竟是不是文字,學(xué)術(shù)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也因此,在此次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中發(fā)現(xiàn)的刻畫(huà)符號(hào)究竟是否中國(guó)最早的文字,還有待于進(jìn)一步商榷。
不經(jīng)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考古學(xué)應(yīng)該是一門(mén)經(jīng)得住寂寞的學(xué)科,因?yàn)閷?duì)歷史蛛絲馬跡的追溯容不得半點(diǎn)馬虎,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也因此,這個(gè)社會(huì)盡管浮躁,傳媒盡管著急,至少還應(yīng)給考古保留一份凈土,容許它靜下心來(lái)慢慢推敲與琢磨,如此方能還原人類(lèi)歷史本來(lái)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