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每個時代都有它的“現代”,我們這里所說的現代又從何時算起呢?具體的界定是有難度的,不過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大致的界限。按我的理解,西方現代文學是從對傳統文學進行變革時開始,也就是從浪漫主義運動時就開始了。其后,《丑的美學》與《惡之花》這兩部作品的誕生則標志著現代主義文學已經有產兒呱呱墜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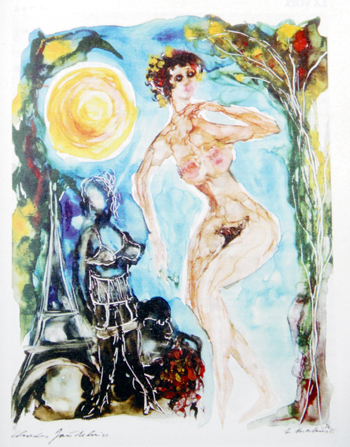 這里講的“現代文學”指的是以現代主義文學為前導的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文學。誠然,每個時代都有它的“現代”,我們這里所說的現代又從何時算起呢?具體的界定是有難度的,不過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大致的界限。按我的理解,西方現代文學是從對傳統文學進行變革時開始,也就是從浪漫主義運動時就開始了。浪漫主義運動中有一支“異軍”,即德國的浪漫派,首先從它那里發出了20世紀文學的先聲,我稱之為“現代主義在母腹中的躁動”。美國的愛倫·坡、霍桑所強調的“主觀”、“內在”,與德國浪漫派有相通的地方。這些都發生在19世紀上半葉。稍后一些,德國的羅森蘭克蘭茲寫了本理論專著《丑的美學》,將傳統的審美標準完全給顛倒過來了!過去西方人共同遵循的審美標準首先是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論”詩學理論,再就是17世紀以來的歐洲古典主義美學律條:理性啦,崇高啦,莊嚴啦,諧調啦,高貴啦,勻稱啦,優雅啦,等等。羅氏寫的則把它們統統給顛覆了!這是1853年的事。四年后,即1857年,法國詩人波德萊爾在詩歌創作實踐中將下層人民的生活,向來“不齒于人”的人如小偷、乞丐、妓女等等的陰暗生活寫入作品,題為《惡之花》出版,這在歐洲文學史上也是個破天荒的大事件。如果將德國浪漫派文學比作現代主義文學在母腹中的躁動,那么,《丑的美學》與《惡之花》這兩部作品的誕生則標志著現代主義文學已經有產兒呱呱墜地了。但這股思潮最終形成大的聲勢還是在那個世紀的80年代,一連發生了如下幾個標志性事件:首先就是法國的莫里亞斯1986年在《費加羅報》上發表文章,用了“象征主義”這一名稱(之前的象征主義創作都是名不正言不順進行的,因此理直氣壯地以宣言的形式發表這樣的文章是需要勇氣的)。另一事件發生在美術界,也在1886年:塞尚、凡·高等后期印象派畫家舉辦了一次重在表現內在情緒的畫展,這次畫展標志著美術界現代主義的起步。三是1884年,建筑界的藝術大師們在布魯塞爾舉行了會議,名為“新藝術運動”,這次會議被公認為是建筑界向現代主義邁進的標志。四是1887年,戲劇界的安托昂(法國)針對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宮廷劇院建造了一座“自由劇場”,這座劇場在形式、規模、布景特別是理念等很多方面都與宮廷劇院大相徑庭,打破了宮廷劇院的貴族氣派和易卜生的“佳構劇”模式,推倒了“第四堵墻”,被認為是戲劇界向現代主義進軍的信號。五是1994年,音樂界的法國鋼琴家德彪西創作了一首《〈牧神的午后〉序曲》,這首曲子被認為是“敲開20世紀音樂大門”的開山祖。這一系列事件意味著西方人的審美意識發生了質的飛躍:瀑布式地從傳統躍入到了“現代”。
這里講的“現代文學”指的是以現代主義文學為前導的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文學。誠然,每個時代都有它的“現代”,我們這里所說的現代又從何時算起呢?具體的界定是有難度的,不過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大致的界限。按我的理解,西方現代文學是從對傳統文學進行變革時開始,也就是從浪漫主義運動時就開始了。浪漫主義運動中有一支“異軍”,即德國的浪漫派,首先從它那里發出了20世紀文學的先聲,我稱之為“現代主義在母腹中的躁動”。美國的愛倫·坡、霍桑所強調的“主觀”、“內在”,與德國浪漫派有相通的地方。這些都發生在19世紀上半葉。稍后一些,德國的羅森蘭克蘭茲寫了本理論專著《丑的美學》,將傳統的審美標準完全給顛倒過來了!過去西方人共同遵循的審美標準首先是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論”詩學理論,再就是17世紀以來的歐洲古典主義美學律條:理性啦,崇高啦,莊嚴啦,諧調啦,高貴啦,勻稱啦,優雅啦,等等。羅氏寫的則把它們統統給顛覆了!這是1853年的事。四年后,即1857年,法國詩人波德萊爾在詩歌創作實踐中將下層人民的生活,向來“不齒于人”的人如小偷、乞丐、妓女等等的陰暗生活寫入作品,題為《惡之花》出版,這在歐洲文學史上也是個破天荒的大事件。如果將德國浪漫派文學比作現代主義文學在母腹中的躁動,那么,《丑的美學》與《惡之花》這兩部作品的誕生則標志著現代主義文學已經有產兒呱呱墜地了。但這股思潮最終形成大的聲勢還是在那個世紀的80年代,一連發生了如下幾個標志性事件:首先就是法國的莫里亞斯1986年在《費加羅報》上發表文章,用了“象征主義”這一名稱(之前的象征主義創作都是名不正言不順進行的,因此理直氣壯地以宣言的形式發表這樣的文章是需要勇氣的)。另一事件發生在美術界,也在1886年:塞尚、凡·高等后期印象派畫家舉辦了一次重在表現內在情緒的畫展,這次畫展標志著美術界現代主義的起步。三是1884年,建筑界的藝術大師們在布魯塞爾舉行了會議,名為“新藝術運動”,這次會議被公認為是建筑界向現代主義邁進的標志。四是1887年,戲劇界的安托昂(法國)針對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宮廷劇院建造了一座“自由劇場”,這座劇場在形式、規模、布景特別是理念等很多方面都與宮廷劇院大相徑庭,打破了宮廷劇院的貴族氣派和易卜生的“佳構劇”模式,推倒了“第四堵墻”,被認為是戲劇界向現代主義進軍的信號。五是1994年,音樂界的法國鋼琴家德彪西創作了一首《〈牧神的午后〉序曲》,這首曲子被認為是“敲開20世紀音樂大門”的開山祖。這一系列事件意味著西方人的審美意識發生了質的飛躍:瀑布式地從傳統躍入到了“現代”。
這之后就產生了一系列“現代”意義上的流派,像象征主義、未來主義、表現主義、達達主義、意識流、超現實主義、后象征主義等。30年代初,由于法西斯勢力的崛起,這些流派曾一度消歇(因為好多藝術家都投身于政治運動了),二戰后,這一藝術變革的能量才又重新釋放出來,而且變革的力度更猛,出現了一些“反戲劇”的戲劇(如法國的“荒誕派”戲劇)、“反小說”的小說(如法國的“新小說派”小說)和“反詩歌”的詩歌(如德國的“具體派”詩歌)等。它們都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這十來年內橫空出世。此外五六十年代在美國還先后出現了“垮掉的一代”詩歌和“黑色幽默”小說。這時期拉美地區發軔于20年代的魔幻現實主義也蓬勃崛起。除了黑色幽默和魔幻現實主義,戰后興起的流派美學上更具顛覆性,可以歸入“后現代”的潮流。“后現代”整體上的起步當以1968年歐洲的學生運動為標志,在音樂、美術、建筑、電影等領域均有不同的表現。我認為它大致呈現出兩個截然相反的傾向:一是走向深奧、艱澀,更具先鋒實驗性質。像瑞士出生的法國建筑家柯布西埃在法國建造的朗香教堂,墻上面有幾個窟窿,屋頂像蓋著一床翻卷著的厚棉被,看起來與教堂毫不相干;悉尼歌劇院也是后現代建筑的代表作,傳統建筑中最基本的要素——頂與墻之間的界限被徹底抹掉了。后現代的另一個傾向是泛大眾化傾向,它不僅形式通俗,內容也切近大眾生活,讓大家感到熱辣、刺激。而且這里的大眾不再是被動的受眾,而是創作主體(包括演唱)的一部分,臺上臺下互動、閱讀與批評融為一體。60年代末,東、西德兩邊的學者幾乎同時推出了“接受美學”的理論不是偶然的,我認為這是平民意識的覺醒在美學上的反映。我曾借用“五四”時期革命家用過的題目“庶民的勝利”寫文章專門探討過這一問題。中國改革開放前也一直提倡大眾化,但那時候的“大眾化”是自上而下灌輸的,喚不起讀者和觀眾像現在這樣的自發的熱情。比如現在的卡拉OK、搖滾音樂,不管你有沒有練過唱,哪怕五音不全,都可以拿著話筒,唱得“死去活來”,臺上臺下打成一片。這在我們那個時代是不曾有過的。當然,也有人說,這樣一來“我們沒有文化了!”(漢斯·馬耶爾語)我不同意這種觀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因為文化形態和樣式也是隨著時代而不斷更新的。“大眾化”之后不是沒有文化,而是老一代人對新一代文化不敏感了,隔膜了,已感受不到當代文化新魅力了!因為固有的文化觀念、審美信息在我們腦子里已經飽和了,新的東西因此很難進得去。我認為文學專家、美學專家都應警惕這一問題,避免隨著年齡漸長而產生排他性。像黑格爾這樣的大家,他對古典主義藝術贊美有加,卻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浪漫派藝術不敢領教,比如音樂。他甚至聽到像貝多芬這樣雄渾絕妙的浪漫派樂曲感覺“像瘋子在井邊跳舞”,難以接受。作為一個欣賞者這樣說當然無可厚非,但作為一個美學家就有失偏頗。我年輕時候也很喜歡音樂,但現在的流行歌曲基本不會唱,唱不像,也學不會,不過我尊重這一音樂形式。因為我高興看到普通老百姓開始真正擁有自己的文化。因此“后現代”的這一種精神,即平民意識的增強還是值得肯定的。這表現在建筑里就是人性化訴求的強調。如現在所說的“詩意棲居”就很人性,故具有“后現代”意識的建筑師都批評現代主義的建筑過于冷冰冰,傳統中的有益部分拋棄得過多等等,而提出城市規劃和建筑“要以人為中心”的口號。“后現代”在文學上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它的多元意識及與之有關的寬容精神。你看現代主義興起的時候流派林立,而且每個流派都打出一面旗幟,發表一道綱領,或提出一些主張,都強調唯我正確,都想稱霸。但“后現代”興起的時候,這種現象就基本不見了。剛才提及的那些流派的名稱都不是他們自己起的,而是教授、學者們給起的,例如“荒誕派”是英國戲劇理論家馬丁·埃斯林起的;“新小說派”是法國哲學家薩特起的;“黑色幽默小說”是美國教授弗里曼起的。這時期的作家、藝術家們顯得散淡多了,他們似乎只想表達自己,卻并不標榜什么。而這正是“后現代”的精神:每個個人的存在都以尊重他人的存在為前提。
以上我們講了19世紀現代主義興起以來的大致趨向。下面再來談談,與傳統文學相較,現代文學到底在哪些方面發生了革命性變化。按照我的視野和知識所及,我想歸納為下面五個方面來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