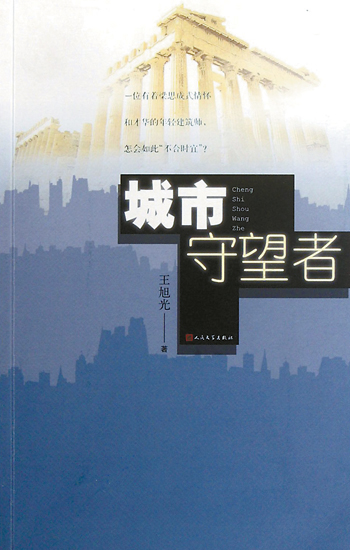
《城市守望者》
王旭光 著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
城市讓理想主義成為雕像
——評王旭光長篇小說《城市守望者》
誰來守護(hù)城市?這其實(shí)并不是一個現(xiàn)代性的問題。英國北部城市愛丁堡幾乎可以象征整個中世紀(jì),而它的市銘卻鮮為人知:“如果不是神守護(hù)著城市,守夜人徹夜無眠也無濟(jì)于事。”中世紀(jì)之后,人文精神如星辰拱衛(wèi)在城市上空,所以美國詩人惠特曼在他的《斧頭之歌》中寫出了這樣的句子:“偉大城市的標(biāo)志是產(chǎn)生偉大的人物,即使有幾座破舊的房屋,仍不失為偉大的城市。”顯然,作為新大陸的詩人,惠特曼心目中的城市還具有清教徒拓荒的性質(zhì),并沒有給建筑留出多少空間,但他那種單純、徹底的人文尺度,至今仍不失為美國城市最富詩意的標(biāo)準(zhǔn)。
實(shí)際上,神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是內(nèi)在一致的,就城市建筑而言,這樣的尺度不僅同樣需要,而且尤其需要。但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特別是在當(dāng)下的中國,所有這些似乎都不過是高遠(yuǎn)的哲思、文化的云霓,很難落實(shí)到城市發(fā)展的地面上。
這就是小說《城市守望者》主人公曾思凡的處境。當(dāng)我們的城市到處都是建筑工地,當(dāng)挖掘機(jī)和吊車的轟鳴前所未有地推進(jìn)著城市化進(jìn)程,誰愿意傾聽城市古老而沉靜的韻律,凝視城市優(yōu)美而曠遠(yuǎn)的天際線呢?或許有之,如曾思凡。這是一個理想化的人物,作者對他的形象塑造,無疑是以建筑學(xué)家梁思成為原型的。從梁思成到曾思凡,兩代建筑師,都是以“思”為旗幟,薪火相傳、寥若晨星地守望著城市的理想之維和人文精神高度。
可以說,這是比較自覺的浪漫主義敘事,更是難能可貴的理想主義頌歌。“城市是人的,城市是有靈魂的,是有生命的!我們必須尋找城市”,一個不僅要守望城市,而且還要尋找城市的人,他差不多已經(jīng)像一個神話英雄。包括他的愛情生活,與其說是現(xiàn)實(shí)的,毋寧說是象征的。亭亭作為曾思凡的戀人和妻子,她和另一個暗戀曾思凡的女孩一起,共同象征了那種林徽因式的“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的經(jīng)典女性之美。
但故事的悲劇性在于,曾思凡并不是梁思成,正如他的戀人們也不是林徽因。前者與后者之間,不僅存在著時代的錯位,更有著出身和聲望的巨大差異。與梁思成顯赫的家世相比,曾思凡只是貧寒的農(nóng)家子弟,一個八級工匠的兒子,而且是靠父親賣血換錢才走進(jìn)大學(xué)校門的。這樣的出身,既是他上升的動力,也是他前行的重負(fù)。經(jīng)驗(yàn)中的創(chuàng)傷和經(jīng)歷中的磨難造就了他特殊的稟賦,有時獨(dú)往獨(dú)來,風(fēng)骨剛健;有時憤世嫉俗,艱澀難近;說正直就正直到偏執(zhí),說堅定就堅定到迂闊。這樣的人,非但無法做到梁思成那樣的寬宏儒雅、深厚淡定,相反卻提供了鮮明的對比。
所以曾思凡的悲劇是雙重的,一是性格與理想的矛盾,二是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距離。這種主觀和客觀、內(nèi)在和外在的雙重命運(yùn),決定了他那會令人想起哥特式建筑的精神形象,既是忠誠于崇高理念的建筑師,又像個孤寂的詩人和虛靜的哲學(xué)家;他內(nèi)心似乎有著堅韌不拔的力量,但在充滿困窘和詭異的現(xiàn)實(shí)面前,卻被消磨得只剩下了脆弱、無奈和憂傷,直到最后被擊垮,成了這個海濱城市的一座似有若無的雕像。
這是城市為自己的理想而樹立的雕像,就像梁思成,是歷史為自己的理想而創(chuàng)造的神話和傳奇。因此就《城市守望者》而言,我覺得它至少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如此集中地描寫了當(dāng)下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tài),二是如此強(qiáng)烈地表現(xiàn)了理想主義精神。
如何理解當(dāng)下中國的知識精英,換言之,如何塑造知識分子形象,盡管斗轉(zhuǎn)星移,社會語境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這仍然是文學(xué)的一個重要課題。《城市守望者》寫了一個可能會成為大師的建筑師,他的隕落似乎揭示了知識精英們的普遍境遇,但小說并沒有對“中國為什么產(chǎn)生不了大師”之類的問題提供簡單的答案,因?yàn)樵谇楣?jié)的起落發(fā)展中,我們看到除了環(huán)境和體制的問題,知識分子作為“人的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不足也被凸顯了出來。如前所述,特立獨(dú)行的曾思凡雖然傳承了大師關(guān)于城市的理想,卻并沒有體現(xiàn)出大師的人格理想。所謂“千年秋草,可以傲霜雪,不可以為棟梁”,足以為這樣的知識分子寫照。但是,相比于那些既不敢傲霜雪也不堪為棟梁的大量所謂“學(xué)院派”或“公共型”知識精英們,曾思凡的形象仍然是高度理想化的,也可以說,他的理想主義是對當(dāng)下某些知識分子人格潰敗的有力批判和狙擊。就此而言,曾思凡式的知識分子更稀缺、更珍貴。尤其在知識分子整體的意義上,特立獨(dú)行者從來都是一種生態(tài)性的標(biāo)志。只有當(dāng)一個時代廣泛容納并充分尊重了這樣“可以傲霜雪”的知識分子,才可能出現(xiàn)一個生機(jī)盎然的社會空間,讓真正“可以為棟梁”的文化大師從中產(chǎn)生。這是小說主人公的別樣生存狀態(tài)給予我們的特殊啟示。
《城市守望者》的可貴之處在于它神話般的主題和彌漫在字里行間的激情:“建筑是文化的上部結(jié)構(gòu),它的下部結(jié)構(gòu)應(yīng)該是信仰”——信仰在上,是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設(shè)計;信仰在下,是浪漫主義的構(gòu)想,但無論信仰在何處,城市發(fā)展的最終目標(biāo),還是如同馬克思所說的,要讓“物化把它的力量交還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