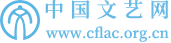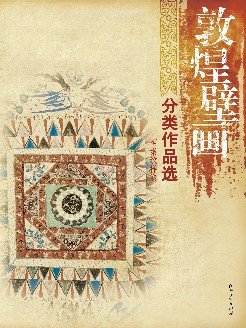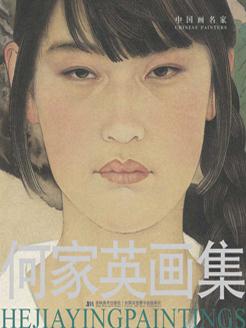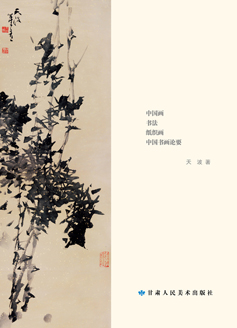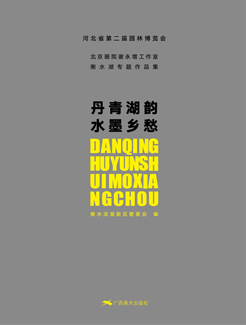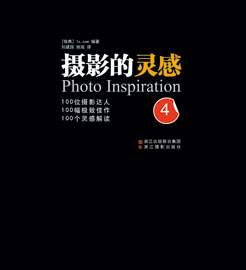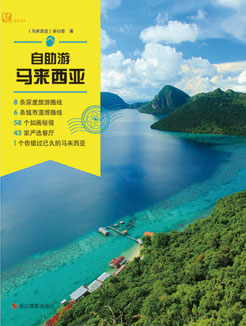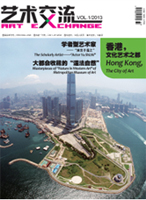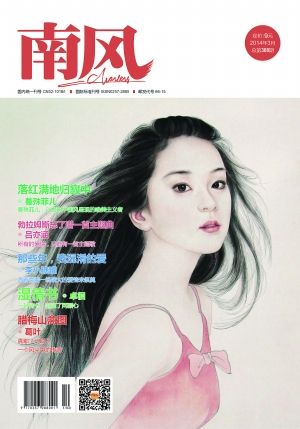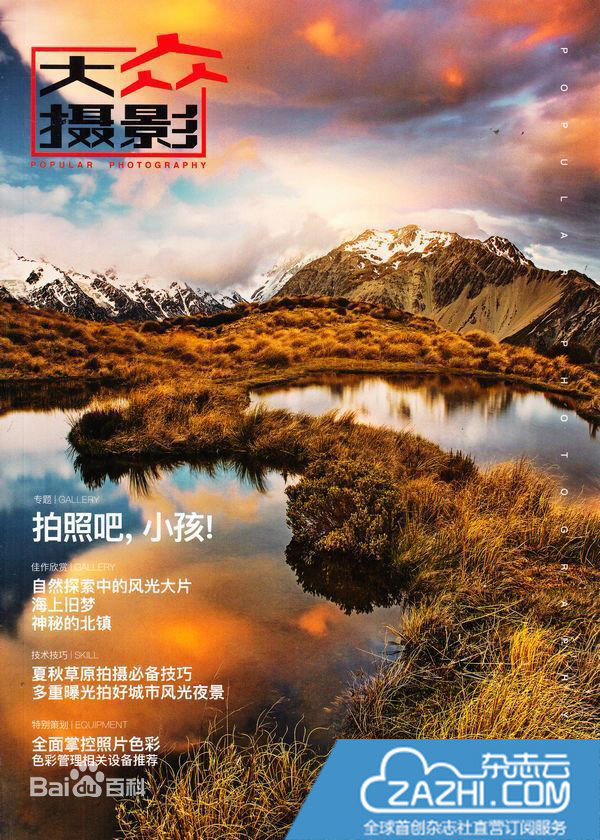把《一九四二》僅僅當(dāng)做一部賀歲檔出現(xiàn)、定位于娛樂消費(fèi)的影片是不恰當(dāng)?shù)模谌魏螘r(shí)間、檔期上映,都是中國(guó)電影人對(duì)中國(guó)厚重歷史、特別是災(zāi)難史的貢獻(xiàn)。

電影《一九四二》劇照
毋庸置疑,《一九四二》是一部飽含誠(chéng)意和莊嚴(yán)的電影。今天大家津津樂道其19年醞釀、11年籌備的驚人數(shù)字,對(duì)于當(dāng)事人、主創(chuàng)者卻是艱難勞碌、堅(jiān)持探尋的人生苦旅。創(chuàng)作終于開始后,拍攝過程的復(fù)雜繁重、工作方式的苦行自律,在今天的國(guó)產(chǎn)片制作中都絕少見到。相比之下,投資如何龐大、演員陣容如何豪華,反倒不再是《一九四二》最可驕傲的部分。我們必須承認(rèn),唯有這樣的制作態(tài)度,才對(duì)得起影片分外沉重的題材。因此,把《一九四二》僅僅當(dāng)做一部賀歲檔出現(xiàn)、定位于娛樂消費(fèi)的影片是不恰當(dāng)?shù)模谌魏螘r(shí)間、檔期上映,都是中國(guó)電影人對(duì)中國(guó)厚重歷史、特別是災(zāi)難史的貢獻(xiàn),因?yàn)闆]有任何其他藝術(shù)媒介能夠像電影這樣,以視覺形象把我們國(guó)家民族的創(chuàng)傷做驚人逼真的呈現(xiàn),從而用巨大的感性沖擊喚起民眾的生存意識(shí)。影片的宣傳語(yǔ)“活下去,走下去”,既是影片中災(zāi)民的命運(yùn),但從生命的本質(zhì)上講,又何嘗不是每個(gè)人的宿命?如果說商業(yè)化的災(zāi)難片釋放著人們?cè)诜ξ渡钪挟a(chǎn)生的莫名焦慮,那么嚴(yán)肅寫實(shí)、制作上乘的災(zāi)難題材電影則與藝術(shù)史上杰出偉大的災(zāi)難題材繪畫、雕塑、文學(xué)等一樣,有助于一個(gè)人、一個(gè)民族的心智成熟、深邃。這個(gè)基本的判斷不應(yīng)偏差,至于“影片在多大程度上做到這點(diǎn)”,應(yīng)該是第二步要探討的問題。
或許是因?yàn)檫@樣一份與生俱來(lái)的使命意識(shí)過于濃重,也因?yàn)獒j釀籌備的過程過于漫長(zhǎng)疲勞,當(dāng)馮小剛導(dǎo)演真正開始把意念轉(zhuǎn)換為影像的時(shí)候,他不止一次表露出了彷徨無(wú)奈的心情,在混錄最終完成后,他自認(rèn):“這部影片對(duì)于我來(lái)說,有點(diǎn)像談了十幾年的戀愛終于扯證結(jié)了婚,新婚之夜遠(yuǎn)沒有當(dāng)初想的那樣蓄勢(shì)待發(fā)魂飛魄散……媳婦也確實(shí)是好媳婦,就是有點(diǎn)不咸不淡。”(馮小剛微博2012年10月8日)顯然,這部影片以及影片之外的經(jīng)歷留給他許多遺憾。如馮的許多言語(yǔ)一般,“不咸不淡”的表述入木三分,耐人尋味。很多觀眾對(duì)《一九四二》期待有年,他們來(lái)看此片前早已看過原作,對(duì)這部分觀眾而言,恐怕也找不出比“不咸不淡”更貼切的詞語(yǔ)來(lái)形容自己感受了。影片的敘事在與那個(gè)年頭、那場(chǎng)災(zāi)難相關(guān)聯(lián)的歷史空間里逐次完成任務(wù),時(shí)間近乎平靜地前行,節(jié)奏舒緩,一切都有條不紊。災(zāi)難的加深幾可量化為存糧的消耗程度和人物的死亡順序,對(duì)熟悉敘事技巧的觀眾來(lái)說,很多事件是可以預(yù)知的。
為了把影片敘述的焦點(diǎn)放在災(zāi)民身上,《一九四二》創(chuàng)作了幾位文學(xué)本中原來(lái)沒有的人物,以東家老范為線索,串起了逃荒的日日夜夜、膽戰(zhàn)心驚。從好的方面看,主創(chuàng)者對(duì)老百姓的熟悉幫助他們把這幾位人物塑造得相當(dāng)合理,幾處細(xì)節(jié)和臺(tái)詞甚至堪稱傳神(這種民間文學(xué)技法正是編劇劉震云的拿手好戲);但從另一方面看,災(zāi)民的苦戲畢竟不是整個(gè)故事的重心,苦戲出現(xiàn)在災(zāi)難表象的層面上,而影片卻是要探討災(zāi)難惡化的機(jī)制和歷史規(guī)律的無(wú)情。
當(dāng)然,為了有合理的拷問機(jī)制的情緒動(dòng)力,影片確實(shí)需要呈現(xiàn)足夠的災(zāi)難場(chǎng)景,而這一點(diǎn)卻又略顯不足。1942年-1943年河南天災(zāi)人禍并發(fā),所謂“水旱蝗湯”,除去最后的湯恩伯,前三種在視覺上都是極端可怕、驚心動(dòng)魄的。影片只是著重提到旱災(zāi),但視覺呈現(xiàn)不足。蝗蟲出現(xiàn)在了影片的宣傳畫上,有意做成當(dāng)時(shí)流行版刻的樣子,影片里卻一只不見。最能顯示饑民生存威脅的莫過于食物的量和質(zhì),也沒有在影片里得到與原著同等分量的表現(xiàn)。
在反思機(jī)制導(dǎo)致災(zāi)難惡化這個(gè)層面上,影片敘事的潛在力量沒有釋放出來(lái),這可能是馮小剛和本片最大的遺憾。我們看到,民國(guó)政府的總裁與官吏沒有被簡(jiǎn)單的丑化和矮化。相反地,影片把他們的行動(dòng)思維邏輯盡可能給出入情入理的解釋,而越是入情入理,就越接近“惡的體制使人作惡”這一命題。于是,不是災(zāi)難的悲劇性,而是災(zāi)難必然、不得不然的惡化,以及這看似不得不然背后的人性盲區(qū),才構(gòu)成凌駕悲劇之上的巨大荒誕感。從美學(xué)上講,對(duì)荒誕的發(fā)現(xiàn)和闡釋,是現(xiàn)代悲劇觀對(duì)古典悲劇模式的革命性超越。對(duì)于《一九四二》來(lái)說,事件的后半程各種力量的粉墨登場(chǎng)、各懷心事,恰恰具備這種現(xiàn)代美學(xué)意義上的荒誕感。如果說《一九四二》在美學(xué)把握上最遺憾的,應(yīng)該就是從荒誕退回到悲情的處理,雖然對(duì)于當(dāng)下中國(guó)電影觀眾的理解和接受,這個(gè)做法可能是有效的。
與此相適應(yīng)的,影片敘述形式主要采取了傳統(tǒng)的全知視角,但又不忍放棄文學(xué)版中的敘述者口吻,于是在影片開端和結(jié)尾部分,保留下了一絲痕跡。如果影片索性采用文學(xué)版的方案,從一個(gè)身處現(xiàn)代時(shí)空的敘述者角度去切入歷史,其實(shí)反倒更容易保持理性反思的態(tài)度,也更便于呈現(xiàn)往事的荒誕。事實(shí)上,影片保留下了文學(xué)版里的第二重?cái)⑹稣摺绹?guó)記者白修德。1942年白修德對(duì)災(zāi)難的記錄、講述,以及第一重?cái)⑹稣摺拔摇睂?duì)白修德和其他史料的發(fā)現(xiàn)和再講述,構(gòu)成了相當(dāng)有層次、有差別、有張力的敘述聲音。而且,由于兩重?cái)⑹稣叨急3至藢?duì)災(zāi)難足夠忠實(shí)的態(tài)度、對(duì)時(shí)空足夠理性的處理,并不至于給今天的觀眾帶來(lái)接受上的困難和障礙。而白修德過早不見蹤跡,是影片版的又一樁遺憾。
電影是遺憾的藝術(shù),《一九四二》也不例外。但相比起《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在表現(xiàn)和反思重大歷史和災(zāi)難方面有著寶貴的進(jìn)步,理智取代煽情更是可喜的變化,這些都不容忽視和抹殺。由于歷史的漫長(zhǎng),中國(guó)有世界上最為深刻沉重的災(zāi)難記憶,我們遲早要面對(duì)這些災(zāi)難,用足夠的智慧和勇氣把它們變作血凝的精神財(cái)富。馮小剛在這條路上先走了一程,盡管他本人感到疲勞,接下來(lái)中國(guó)電影卻遲早要“走下去,拍下去”。從電影和電影人的文化屬性來(lái)說,這也是我們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