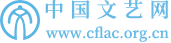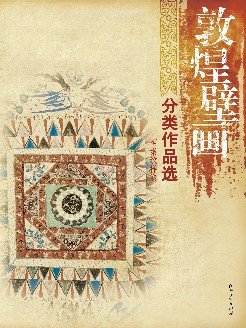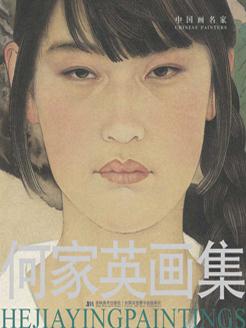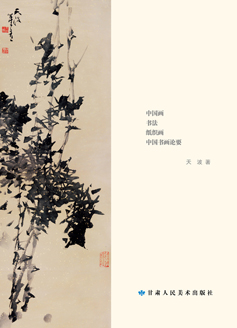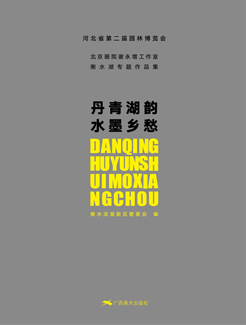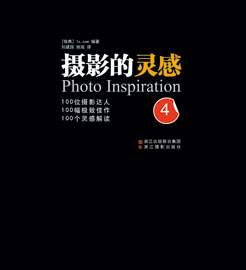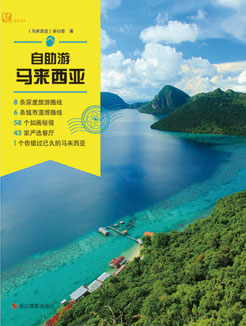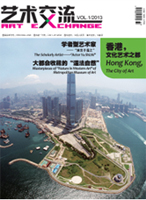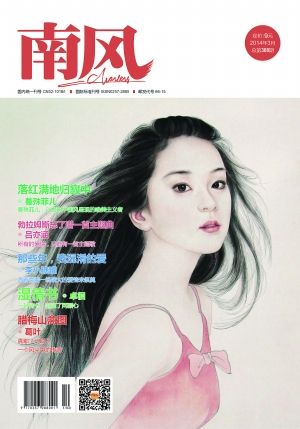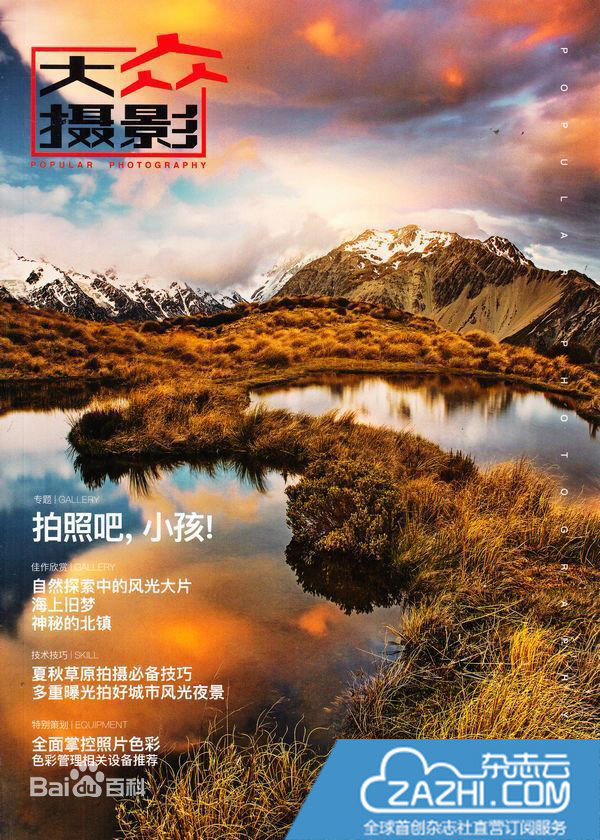劉成紀(jì)
北京師范大學(xué)哲學(xué)與社會(huì)學(xué)學(xué)院教授,美學(xué)研究所所長(zhǎng),價(jià)值與文化中心研究員,F(xiàn)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編委。兼任北京大學(xué)美學(xué)與美育中心教授,澳門(mén)科技大學(xué)講座教授,中華美學(xué)學(xué)會(huì)理事。

日本街景
雖然,我們每天都在渴望生活中美好的一切,比如天際一抹粉色的晚霞,或者少女在風(fēng)中一掠而過(guò)的媚眼。但事實(shí)上,美也許并不是好東西。
記得去日本參加會(huì)議期間的一個(gè)夜晚,因?yàn)榧影嘹s制一份文件,錯(cuò)過(guò)了吃晚餐。至晚上10點(diǎn),突然想到賓館附近的居民區(qū)走走,并順便找個(gè)小館子將轆轆的饑腸裝滿(mǎn)。
夜晚的京都很寧?kù)o。尤其在遠(yuǎn)離馬路的居民區(qū),燈光暗淡,行人稀少,這又使寧?kù)o中透出幾分冷清。
走過(guò)一條小街,拐彎處有一家居酒屋。門(mén)雖然掩著,但里面依然有燈光。于是推開(kāi)房門(mén),便看見(jiàn)一個(gè)中年食客,正和近于老年的老板及他的兩個(gè)女兒閑聊。
店主人很熱情,但他的熱情我卻一句不懂。記得出發(fā)前,我曾經(jīng)告訴會(huì)議的主辦方,自己一句日語(yǔ)不懂,可能到時(shí)候只能用微笑應(yīng)對(duì)各種困難的場(chǎng)面了。他的回答也很幽默,說(shuō):東亞人交流的最好方式就是微笑,it’s enough!
好在,日本人普遍教育程度較高,尤其是戰(zhàn)后一代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說(shuō)上幾句英語(yǔ)交流。于是,一切變得基本順暢。點(diǎn)了一份面,一份菜,便開(kāi)始大嚼。期間,看到鄰座的中年食客喝著日式的清酒挺享受,于是也要了加冰的一杯,慢慢喝起來(lái)。
日本的居酒屋是賣(mài)散酒的。這種清酒口感一般,也只有25度,但倒很容易激起人說(shuō)話(huà)的興致。于是和屋子里幾位日本人有一搭沒(méi)一搭地閑聊起來(lái)。日本下層民眾倒沒(méi)有知識(shí)階層那么多的客套,話(huà)題也樸實(shí),無(wú)非是“相見(jiàn)無(wú)雜言,但道桑麻長(zhǎng)”的一類(lèi)。聽(tīng)著也說(shuō)著,不知不覺(jué)就飲了三大杯。
出得門(mén)來(lái),周邊世界有點(diǎn)恍惚。抬頭一望,一彎清月高懸于天邊。其中,恍惚與酒精的作用有關(guān),清月則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在那里懸著,似乎與夜行者此時(shí)此刻的心境或際遇缺乏必然的關(guān)聯(lián)。
但身處異域,這彎清月依然是讓人感動(dòng)的。遙想起張孝祥對(duì)洞庭月夜“表里澄澈,肝膽冰雪”式的體現(xiàn),所謂的感動(dòng)也就慢慢地變成陶醉了。

日本料理
最近我常常認(rèn)為,審美也許是一種病吧。所謂的忘我或陶醉,往往是以人對(duì)自己當(dāng)下真實(shí)際遇的失憶為前提的。對(duì)于執(zhí)業(yè)醫(yī)生來(lái)講,這很可能是一種由情感刺激而起的生理性病變。世界上因美致病的例子很多。記不清哪本清代筆記小說(shuō)中曾講過(guò),一個(gè)貴族少女因讀《紅樓夢(mèng)》而起了春情,最后抑郁至死,但這并不是中外歷史中的孤例。在現(xiàn)代,也有據(jù)說(shuō)游覽意大利佛羅倫薩的游客,看過(guò)米開(kāi)朗基羅西斯廷教堂的壁畫(huà),也會(huì)數(shù)周迷亂。這被稱(chēng)為因藝術(shù)而起的“佛羅倫薩癥”。
我不想夸大京都之美的感染力。無(wú)論是它精致入微的園林還是美術(shù)館里的藝術(shù)杰作,我欣賞,但如果說(shuō)達(dá)到了非理性的沉迷或陶醉,顯然也有些矯情和夸張。但是我想,在日本,美對(duì)于人和生活的作用卻是值得深刻反思的。我總感覺(jué),這個(gè)民族有種審美中毒的癥候,它鑄成了古代日本讓人嘆為觀止的藝術(shù)化生活方式,但也應(yīng)為這一民族帶來(lái)了諸多與人性自由相背謬的負(fù)面影響。
比如,看日本園林,幾乎是每一根草都是被認(rèn)真梳理過(guò)的,幾乎是每一棵樹(shù)上的葉片都受到了園藝師的特別關(guān)照。這是一種讓人無(wú)法言喻的細(xì)膩,但也由此極易讓人想到中國(guó)古戲文中一個(gè)充滿(mǎn)譏諷的段子。說(shuō)一個(gè)禿子光光的頭頂上剩下了一根頭發(fā),這頭發(fā)讓他珍愛(ài),也讓他憐惜。于是,睡前梳洗這根頭發(fā),起床后對(duì)它進(jìn)行細(xì)致入微的護(hù)理,就成了每天必做的繁瑣功課。于是,一根頭發(fā),也就成了他的事業(yè),他的人生,直至終老。
這根頭發(fā)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日本園林的故事。記得2001年在京都相國(guó)寺,就曾經(jīng)在墻角的位置發(fā)現(xiàn)一根被精心打理過(guò)的草。這根草長(zhǎng)在泥土里,但草根部的周?chē)鷧s如禿子的頭頂一樣一塵不染。當(dāng)時(shí)我是深感震撼的。真難以想象,對(duì)這根草的護(hù)理,每天得花費(fèi)園林師多少時(shí)間和精力。
日本人注意細(xì)節(jié),也表現(xiàn)在人際交往和飲食中。會(huì)間,受主辦方邀請(qǐng),吃了一次著名的京都料理。席間先上了一道烤過(guò)的稻穗,一粒粒將稻米從殼子里摳出來(lái)再填進(jìn)嘴里,確實(shí)是對(duì)人的耐心的重大考驗(yàn)。然后,一道道菜端上來(lái),每一道菜的菜量都少得驚人,同時(shí)菜的數(shù)量也多得驚人。于是吃日本料理的過(guò)程,極類(lèi)似于螞蟻搬家式的艱難跋涉。最后,這星星點(diǎn)點(diǎn)的菜肴終于被全部搬進(jìn)了胃里。于是集腋成裘,倒也飽了。
注意細(xì)節(jié)是一種巨大的優(yōu)點(diǎn),尤其是與凡事習(xí)慣于胡里馬哈、大差不差的國(guó)人相比,更值得展開(kāi)深刻的反省。但是,就人而言,往往習(xí)慣于在芥子殼里做道場(chǎng),便會(huì)疏忽芥子殼之外的廣大世界,一味執(zhí)拗于微觀便會(huì)導(dǎo)致對(duì)宏觀世界的遺忘。這種缺少視野和格局、抓芝麻丟西瓜的性格,對(duì)日本人的影響是致命的,既表現(xiàn)于藝術(shù)創(chuàng)造也表現(xiàn)于現(xiàn)實(shí)政治。許多中國(guó)人,一方面佩服日本人的細(xì)膩,另一方面又嘲諷日本人缺乏男性的大氣和格局,甚至據(jù)此稱(chēng)其為“小日本”,原因概出于此。

日本枯山水庭院
在美學(xué)方面,日本人情感細(xì)膩,感覺(jué)洗煉。東山魁夷在述及中日繪畫(huà)的差異時(shí)曾講:“日本風(fēng)景畫(huà)具有西方與中國(guó)所沒(méi)有的一個(gè)特點(diǎn),就是往往不從廣闊的視野把握風(fēng)景,只是將大自然的一小部分作為作品的主題。這大概可以稱(chēng)為‘花鳥(niǎo)式的風(fēng)景’,就是把從近處看到的一部分自然風(fēng)景構(gòu)成畫(huà)面。這種畫(huà)面的構(gòu)圖很特殊,沒(méi)有遠(yuǎn)景、中景、近景的設(shè)置。只有近景。這可以說(shuō)是出于裝飾性的感覺(jué),但正如一棵野草也能表現(xiàn)大自然的生命,也是日本人熱愛(ài)自然的象征。捕捉大自然微妙變化的敏銳感覺(jué)正是日本人獨(dú)特的纖細(xì)銳利神經(jīng)的體現(xiàn)。”(《與風(fēng)景的對(duì)話(huà)》)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細(xì)膩與缺乏格局,與藝術(shù)上表現(xiàn)出的特點(diǎn)是一致的。
真不知道是日本人的性格造就了日本藝術(shù)的特點(diǎn),還是其藝術(shù)特點(diǎn)造就了民族的性格。但可以肯定的是,對(duì)于這個(gè)愛(ài)美的民族,藝術(shù)應(yīng)該是這種特征的極致性反映,并反向?qū)ζ涿褡逍愿裥纬勺儽炯訁柕膹?qiáng)制和規(guī)定。我堅(jiān)持認(rèn)為,日中近世園林的營(yíng)造,是中古畫(huà)中的山水意象訴諸實(shí)踐的產(chǎn)物,是將表現(xiàn)于卷軸并懸于墻壁的畫(huà)中山水向現(xiàn)實(shí)的物化兌現(xiàn)。進(jìn)而言之,日本家庭的營(yíng)構(gòu)和布置,又是對(duì)貴族或士人園林的進(jìn)一步移借或向日常生活的蔓延。據(jù)此來(lái)看,是日本藝術(shù)的細(xì)膩造就了日本人日常生活的細(xì)膩,也是日本藝術(shù)、園林的缺乏格局鑄成了日本人性格和日常審美方式的缺乏格局。這樣,原本是讓人自由解放的藝術(shù),在日本,則成了對(duì)人的日常生活行為進(jìn)行強(qiáng)制性建構(gòu)的原則和力量。
于此,美的自由解放的特性,也就徹底轉(zhuǎn)換為專(zhuān)制性。藝術(shù)作為日常生活必須遵從的范式,也就成為壓抑人性、鉗制自由的異化式力量。
在這種背景下可以看到,美和藝術(shù),與其說(shuō)在成就著人性,倒不如說(shuō)在扭曲著人性。與其說(shuō)讓人性開(kāi)敞,倒不如說(shuō)是將人裝入了藝術(shù)范式的芥子殼。如果說(shuō)日本人的局促和小氣是在芥子殼里做道場(chǎng),那么它的藝術(shù)顯然起到了極其負(fù)面的示范作用。
一個(gè)民族,在其文明的極限處,極易被美挾持或綁架,以致于日常生活中為維持一種反人性的優(yōu)雅,而變得縮手縮腳。真不知道這是一個(gè)民族的幸還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