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那有聲有光的“人與文”
記張暉與他的《無聲無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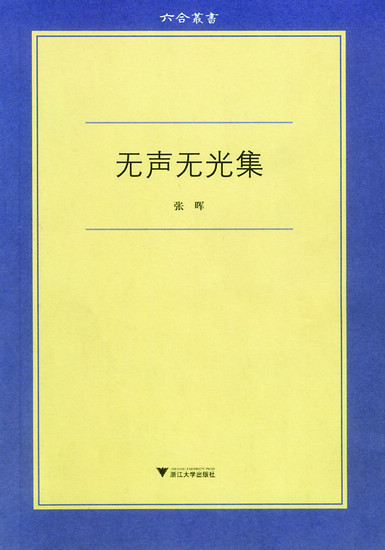
“在嘈雜的市聲與閃爍的霓虹中,面對無聲無光的石塔,我日復一日地讀書寫作,只為輯錄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正是書中這些有聲有光的人與文,陪我度過了無聲無光的夜與晝。”《六合叢書:無聲無光集》系“六合叢書”第一輯的最后一本,是作者張暉近年撰寫的中國文史隨筆,在其自序中這樣寫到。這也是張暉生前所出的最后一本書,隨著他的猝然英年早逝,這也已成了他最為世人所知的著作。更為可貴的是,和他別的著作不同,這是他唯一的自選論文隨筆集,其中不僅可見其學問的關注重心,事實上也處處透露出他自己的學術情懷。日前,“閱讀鄰居”在北京的讀易洞書店舉行了有關閱讀“廣度”話題的討論,并就張暉的《無聲無光集》做了有意味的探討。特別是,張暉的夫人、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張霖也參與了討論,談及她眼中的愛人,并深情地追憶了張暉的治學與為人。
1.“他的手上永遠有一本書在看”
“關于張暉的學術范圍,他在編輯《無聲無光集》時也基本把他的學術范圍囊括進去,他做的就是明清時代的詩學和詞學、民國學術研究,這是他最感興趣的三個部分,在《無聲無光集》中他閱讀的所有書籍都是跟這些領域相關的。張暉在治學的過程中,他的讀書范圍很大的,因為在我們北京的家里,他的藏書就有兩萬冊,上海崇明的家里還有一萬多冊的圖書。”張霖談到。因為張暉并不是富家子弟,他的父親經常說起來,他白天上班,晚上要去釣黃鱔補貼家用,為讓張暉讀書。在張霖看來,張暉到各個地方去游學的過程中,他們的生活地圖也基本全是靠書店串聯的,張暉還曾經幻想過說什么時候把去過的書店拍下來,作為他的讀書地圖。
張暉讀書量相當之大,在張霖母親的印象里面,她有時候覺得張暉不是一個好女婿,因為到家里面來的時候,沒有感覺到女婿和丈母娘之間有貼己的交流,因為張暉永遠手上拿一本書。“她會覺得他是不是不愿意跟我們說話,我說不是,他就是這樣生活,后來我媽媽也習慣了,因為她發現他確實不管做什么手上永遠有一本書在看。后來我母親也習慣了,她知道張暉只是在讀書,讀書的時候也同樣可以跟她聊天,她不會覺得是拒絕她的方式,而是他的生活方式就是這樣。”張霖說。
2.“他選擇研究的都不是這個時代的主流”
《無聲無光集》分四輯。第一輯寫唐詩宋詞中的掌故,如唐朝酒價、南明秘史、姜白石的愛情、元縝的夢。第二輯談近代學者的處事與治學,如怎樣理解黃侃、俞平伯的俗世情懷。第三輯是評論文字,如書院的知識生產與清代人文圖景、唐詩的傳承等。最后一輯為作者對陳國球、吳庚舜、徐公持三位先生的訪談。張霖說,“張暉到了一定階段以后發現,知識的積累只是一個量的增加,不能推進學術的深度,所以他的研究領域相對來說再專門,還是有前輩批評他說你做得太雜了,他也一直在試圖尋找他一貫能夠堅持下去的問題。最終他通過他對于人生、對于世界、對于學術的思考,他都不斷地追問,他再把他的知識向前推進。他也是要回答學術到底對這個世界還有什么意義,這樣的方式把他的研究和整個世界聯系起來。他最后的期望是,他的廣度應該不僅限于文學領域,他是希望讓他的書,讓所有對知識有興趣的人,都能思考知識與學術或者與世界的關系。雖然他自己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但是他一直有一個入世的情懷,所以他對于俞平伯的很多討論,對于黃侃的很多討論里面,他關注的是他們對于人生、對于世界的抱負,他關心的是這個問題,這也可能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
張霖感嘆說,“我原來讀《無聲無光集》的時候沒有特別多的感覺,因為很多時候我還會幫他改一改,但是現在我再讀的時候發現,很多真的是他個人的夫子自道,把他的情懷、他的生命都融入到研究對象里面去了。有朋友看過后談到,他選擇研究的人好像都不是這個時代的主流,都是一些選擇了很奇怪道路的人,都是不被世界理解的人。張暉做這樣的工作,他本人也是有這個明顯感覺的,他不被認同,但是他又感覺到這是他要做的事情,他不斷希望證明它的價值。”
3.“他的痛苦來自于他的自我期待”
“他被承認得特別早,很早就有人說他是天才。但是他同時感到強大的阻力,有的時候他感覺到別人在看笑話,或者等待他的失敗,他可能會有這樣的壓力,他有時候很怕做不成,期望越高壓力越大,他非常擔心做不成。而且還有一個現實問題,張暉不是富家子弟,他看到他父母對他的付出非常大,而且對整個家族來說,他可能是最有出息的人,他有時候會覺得自己有重振家族的使命,所以他特別期待通過他的學術換得一些直接的物質條件的改善,但是包括到現在為止他父親都沒看到,對他父親來說這是一個‘幻滅’,他得到的這些名聲不能實際地幫助到他的家庭。作為我來說,我也做這個行業,我可以理解,我不需要這些,但是當我說不需要的時候,他會覺得他虧欠的更多,而且他通過學術的方式報答所有人,老師對他的期待、家庭對他的期待,他作為兒子的責任、作為丈夫的責任、作為父親的責任,都是通過學術達成。”張霖對此談到,“他的各種各樣的痛苦,有時候來自他的自我期待,他的期待相當高,但是這個過程非常難,而且是在短時間內不可能完成的。”
張霖查看張暉生前的文檔,“他本來今年計劃出版的書就有四五種,他的遺稿三種,八本書,還有他的一大堆著作目錄,大概有十幾、二十本書放在那里準備寫,直到(去世前)那天晚上他問我的問題都是下一本書要寫什么,當然他也可能是進入到學術爆發期了,他的想法特別多,有時候就像穿上‘紅舞鞋’一樣,他停不下來,非常著急地想把這一切都寫出來。你幾乎都想不到他這種勞動強度,到最后他幾乎每天睡眠時間不足4小時,因為白天的時候孩子在鬧,他那時候就不停地敲材料,所以我現在看到他所有的遺稿都是材料,白天敲材料,只有晚上10點孩子睡了之后才是他的時間,通常一般要工作到早上3點鐘才睡覺,早上小孩子起得又早,起來之后就要找父親玩一會兒,所以他的健康受到嚴重損害,再加上種種內在的壓力。社科院雖然環境不算好,但是對張暉還是蠻器重的,他自己也有這個感覺,但是有時候領導越器重他,他又轉成壓力,他會擔心對不起所有人。”
4.“因為他有一個理想世界在那里”
“張暉為什么走到這一步,可能他開始得早。確實,他治學的這個志向就是在十幾歲的時候確立的。那時候可能大多數人都是挺懵懂的,我們進入學術也是基本上大學畢業,進入研究生階段才開始考慮選擇什么樣的道路,而張暉則是在十幾歲的時候‘開蒙’的。這個確實挺奇怪,我到現在也百思不得其解,因為他們家里也沒有做這方面的人,都是普通的工農家庭,雖然有一些書籍,但是這個興趣是怎么來的,真的很神奇。當然張暉讀書的愛好很早,而且他很勇敢,他開始向前輩學者寫信,他有問題就去詢問他們,跟他交往比較深的就是施蟄存先生,都是崇明人,他經常去施老家里玩兒。他在中學時代、大學時代都經常去,我想可能這對他的影響非常大。后來他高中時候開始給卞孝萱先生寫信,卞先生可能對他的影響非常大,所以他會選擇南京大學,進入南大以后看到他原來讀的這些書里面的名字,都變成活生生的人在他面前的時候,他會有極大的振奮。但是越深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他發現這些活生生的人站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們也會有很多虛無的感受,也會有很消極的內容呈現出來,這些情況對他也是致命的打擊,所以他一直在絕望和希望中徘徊。我在想:他早慧的這種痛苦給他帶來的東西,有時候真的想不到,我到后來讀他日記的時候才看到。前輩學人的一些頹唐,或者他們的一些幻滅,對他的打擊特別大,不像我們覺得世界就是這樣子的,但是張暉有一個理想世界在那里,他有一個極大的痛苦感。”張霖講道。
“為什么說他有‘天才之痛’,一方面人人都說他是非常優秀的,這是在業內。但是另一方面他感覺不到優秀給他的回報,所以他的成就感越來越低,尤其到社科院以后,他的落寞感特別強,所以才會有《無聲無光集》這樣的名字出來,因為他有‘無聲無光’這樣的感受。”
5.“他希望發現中國的真問題”
“張暉有這樣一個想法,因為也是受到海峽兩岸及香港地區,特別是大陸主要是‘章黃學派’的影響,他一直有一個很強烈的跟他們對話的愿望,包括他做詩史的時候,其實是在回應陳國球老師做的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話題。他的回應就是,他不是要否定抒情傳統,但是站在大陸的教育背景下,我們怎么樣從現實主義走到所謂的浪漫主義,我們閱讀的立場是怎么樣來理解抒情的,在他的《帝國的流亡》里面,這時候他的想法相對成熟了,他想做的是把中國傳統學術里面的義理、考據、辭章,或者我們現在說就是文獻、理論,對于文本的細讀,把這些東西融合起來,交織在一起,從文獻、考據出發,發現中國的真問題。對于張暉來說,文獻對他來說是美的,他想通過文獻的方式把義理和文本融合在一起。”張霖對張暉的學術理解十分深刻,“其實,《無聲無光集》是他學術想法的一些邊角料,但是他做這些小文章的時候也很用心,因為他希望每個作品都能有他對于學術的追問在,他一直有這樣的追問,他每篇文章都在做這樣的事情,所以他會這么用心用力,最后把自己耗盡了。”
(編輯:蘇銳)
| · | 誰為神州惜此才——悼張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