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市場、品牌策略與明星類型

【“中產”市場】
調查、研究國內中產階層的消費興趣,應當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內新生代電影的工作方向。
在為數不多的第五代導演“華麗轉身”,并成功完成對奇觀電影的檔期劃分與市場割據之后,反觀第五代導演的接班人,當下傳統院線營銷體系之內留給新生代導演用于騰挪的空間相當有限。更大的挑戰還在于由于P2P(Peer-to-Peer,點對點)技術在網絡世界的普及,網絡免費下載令新生代導演的電影血本無歸。隨著產業環境逐漸走向規范,一批主流視頻網站先后參與到電影后期發行,甚至主動參與到內容產業的核心建構,這對傳統的電影營銷來說是一種豐富,同時也是挑戰。當“播客”、“視客”與“視頻代”等“后新生代”影像群體大量涌現,曾一度通過網絡免費觀看為新生代電影積累的潛在文化資本也逐漸被更年輕的一代所分流,新生代導演面臨的問題更嚴峻。
早期的新生代導演將其觀眾定位為都市青年社群與高等院校的學生一族,十余年之后,這些文化擁躉群體的大部分業已構成當下社會“中產階層”的30歲、40歲群體。“中產階層”的內涵并不僅限于經濟收入,本身還體現并負載著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的價值訴求。與西方的中產階級相比,兩者在社會整體結構形態與身份認同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性。中國的中產階層并不像西方中產階級那樣具有強烈的文化保守心態,他們依然時時遭遇現實生活的焦慮與不安全感。面對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重壓,中產階層亟須尋找情緒表達的通道。
新世紀前后10年間,“前”中產階層曾經視新生代電影為文化代言,并以此為標志將自身與其他群體區分開來。時至今日,這個龐大的群體成為社會中間序列,成為在電影院消費的主流人群。他們希望自己的影像代言者能夠保持跟進,繼續反映他們的生活現實、人生夢想與情感苦惱。與此心理訴求相呼應,《美麗新世界》率先講述發生在進城農民身上的都市奇遇。主人公張寶根白手起家,在通過勤奮勞動獲取成功的同時也贏得了都市女性的愛情。從這場中國式“阿爾杰”如神話般飛黃騰達的命運變換中,隱約嗅出部分新生代導演的中產趣味轉向。此后相繼在《綠茶》《左右》《誰動了我的幸福》《重來》《杜拉拉升職記》《無人駕駛》中進一步發酵為大衛·波德維爾所激賞的中國式“中產階層電影”。而在《瘋狂的石頭》《雙食記》《瘋狂的賽車》中,大量黑色電影元素的摻入又進一步強化了影片的喜劇化自嘲與溫和的批判色彩,其票房上的成功亦非誤打誤撞。因此,調查、研究國內中產階層的消費興趣,應當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內新生代電影的工作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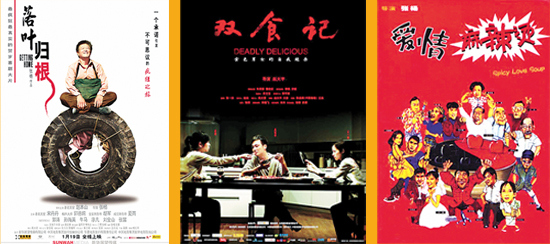
【品牌策略】
在藝術片發行商眼中,將“中國制造”的電影大品牌概念立起來,中國影片才能在國際市場上不被血腥壓價,從靠“我很便宜”轉向“我很值,又好看又不貴”。
中產階層受眾的品牌意識較為明確,電影商品也不例外。目前在這一群體中建立起品牌認同與美譽度的新生代導演寥寥數人中,寧浩憑借“瘋狂”系列良好的市場口碑首當其沖,張一白、張揚、阿甘以各自較為鮮明的類型市場定位緊隨其后。他們共同構成了新生代導演類型化創作與國內市場運作較為成功的第一梯隊。
賈樟柯、管虎與陸川屬于第二梯隊。賈樟柯借助自身的國際影響力與西河星匯獨特的運作模式,能夠成功獲得國際融資與豐厚的商業回報。《無用》《二十四城記》與《海上傳奇》走植入性廣告與城市形象貼牌路線,雖然國內票房慘淡,但對導演來說,只要能通過國際發行收回成本,其盈余足以保證下一部電影的投資,這本身已屬成功。賈樟柯的藝術追求決定了他能夠較為輕松地繞開傳統商業片的道路,但他的個人品牌效應早已被充分商業化了,這也使我們對賈氏商業大片《在清朝》的市場運作充滿了期待。問題在于,專屬賈樟柯電影市場的“體外循環”運作具有獨特的唯一性,對其他新生代導演的市場開發并不具有典型的借鑒意義。陸川憑借《南京!南京!》步入億元票房俱樂部,能夠躋身《建黨偉業》導演組,也是對其新主流電影創作能力的肯定。
第一梯隊與當下中國電影票房市場的對應度最高,第二梯隊稍遜之。而以王全安與王小帥為代表的一批導演如同“隔岸觀火”,屬于固守藝術電影陣營的第三梯隊。他們的作品鞏固了國際藝術片市場里的“中國”概念。而在藝術片發行商眼中,將“中國制造”的電影大品牌概念立起來,中國影片才能在國際市場上不被血腥壓價,從靠“我很便宜”轉向“我很值,又好看又不貴”。對他們來說,需要在國際上尋找能夠直接抵達目標觀眾或片商的有效媒體進行宣傳;而對相關管理部門來說,可以利用“中國制造”的低成本優勢,建立一個有品牌特征的、能夠專門從事推廣此類影片的國際電影發行公司,如法國電影聯盟、日本的UNIJAPAN(它同時還是東京電影節的主辦方)、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FIC),借助官方或非官方的力量營造國際電影市場對中國新生代藝術電影的注意力。
此外,新生代電影市場的明星策略也值得考量。當前,明星已經成為世界電影產業運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近年來好萊塢“明星票房論”逐漸式微,但對于較不成熟的中國電影市場來說,觀眾仍然對明星抱有較高的期待值。
早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新生代導演就開始嘗試明星市場路線。《愛情麻辣燙》有呂麗萍、濮存昕、徐帆等內地實力派明星參演,知名歌手李宗盛、周華健、趙傳也加盟該片,為影片的票房奇跡增色不少。《落葉歸根》作為東北笑星趙本山試水大銀幕的商業片,邀請相聲演員郭德綱、香港影星午馬與內地的胡軍、孫海英、宋丹丹等友情出演。《無人駕駛》有劉燁、陳建斌、林心如與胡一虎等人出演重要角色,再次印證張揚商業噱頭十足的明星“串燒”策略,一方面可以提高影片的公眾知名度,另一方面也讓制作方通過良好的人脈關系,以“客串”、“友情出演”等方式,控制日益高漲的明星參演成本。

【明星類型】
新生代電影參演演員類型分為:藝術氣質、異類明星、精靈表演。
根據演員參演作品的數量與角色分量,可以作出以下類型概括:
其一,代表了早期新生代藝術電影氣質的青年明星,當屬賈宏聲、高圓圓與余男。賈宏聲是新生代早期都市青年男性“銀幕詩人”形象的典型代表。《極度寒冷》中的憤青齊雷最終成為自己藝術創作的犧牲品。賈宏聲更在《昨天》里以真實面目示人,主動剝離專業演員的藝術外衣,從一個“表演的明星”進入“文本的明星”,呈現出明星作為真實社會人“神經質”的苦悶一面。最終他將其主演影片對冷漠社會的理解與拒絕,直接帶入了個體的現實生活。
高圓圓與余男分別代表了新生代電影對女性明星銀幕形象的兩種矛盾性認同:前者是“清純女孩”的本色氣質。從《愛情麻辣燙》開始,高圓圓的青春形象一直延續下來,直到《南京!南京!》才開始出現松動。而演員銀幕形象的堅守與轉型都源自影片題材的要求。余男是“多面人”的天賦型演員。余男出身童星,她的精湛表演常常能夠激發導演的創作靈感。憑借多項國際國內電影節影后的殊榮,這位“中國第六代導演御用演員”在簽約經紀公司CAA的幫助下逐步走向國際市場。有趣的是,美國CAA中國區總經理就是前藝瑪電影公司的創辦人羅異。
其二,郭濤、徐崢、黃渤與姜武屬于新生代電影明星中較具有喜劇類型氣質的男性演員。郭濤、徐崢與姜武均為優秀的青年話劇演員,參演一系列新生代電影使他們為觀眾所熟知。黃渤以草根身份入行,其黑色幽默的表演風格深受觀眾喜愛。由于近年來中低成本喜劇電影市場的火爆,他在2009年創造了一年有6部主演的影片進入大銀幕的紀錄。這些演員不屬于“耀眼”的明星,觀眾更關注他們的演技,其銀幕形象是否符合“男性氣質”倒在其次。
其三,徐靜蕾與趙濤是新生代女明星中的異類。兩位演員的成長與走紅都與新生代電影的發展息息相關。前者從《我和爸爸》開始嘗試由演員到編劇、導演、制片的轉變,其明星形象具有更為博雜的身份內涵。后者以非職業身份成為賈樟柯《站臺》之后所有劇情類電影的主角。
其四,周迅與莫文蔚屬于與新生代電影短暫交集的一類明星。周迅借助“精靈”風格演出,迅速在電影圈走紅。值得討論的是,這種“精靈”氣質強化了銀幕身體的表演性,將其塑造為被“凝視”的欲望客體,與此同時,其個人的演技能力卻被忽略了。
周迅曾經幾乎是跑龍套般地在某片中演了寥寥幾場戲,然而演員一襲紅色連衣裙隔著玻璃窗的“看”與“被看”,其視覺刺激強度得到了極度放大。顯然導演與演員對此都有一定的表現自覺。
周迅此后接拍的商業大片都不間斷地復制銀幕女性的身體景觀,從《如果·愛》《畫皮》到《風聲》《孔子》,莫不如此。莫文蔚成名在前,她與新生代導演的交集屬于類型片意義上的職業化合作,反過來說,也對新生代導演執行較規范的明星工業化運作提供了一些實際經驗。
(編輯:孫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