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海投來的關注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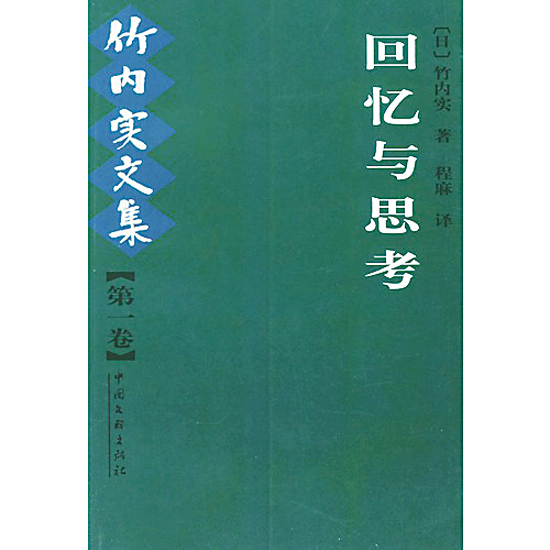
《竹內實文集》 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
日本著名學者竹內實,從1953年起,五十余年來一直從隔海相望的島國,向中國投來關注的目光。持續時間之長,而且涉及范圍之廣,用的功夫之深,可以說創造了海外中國學研究的記錄。他密切追蹤中國的政治變化和社會變革,而為了弄明白這些變化和變革的原因,他又深入到中國的歷史和傳統之中;由于他個人的興趣所在,他對中國自古以來的思想、文學、文化的演變和發展,特別是對現當代中國思想巨擘魯迅和毛澤東的著作和思想,也進行了深入的解讀。他的研究卓有成效,在日本、在我國和國際上都很有影響。海那邊投來的眼神,有時比我們“身在此山中”還看得透徹,畢竟常常是“旁觀者清”啊!
勾畫中國社會現實的圖景
隔著“一衣帶水”,來看中國的社會現實,能看到些什么呢?恐怕是一片混沌模糊吧。中國社會那么錯綜復雜,那么變動不居(特別是自晚清以來),簡直就是“亂花漸欲迷人眼”。
可竹內實經由幾個主題來觀察和分析中國社會,中國社會就在他面前變得逐漸清晰起來。他梳理中國革命的發展脈絡,關注在中國社會舞臺上先后活躍過的帝王、官宦、儒臣、軍閥和文人,甚至將眼光投放到都城、城墻、陵園、建筑乃至茶館等我們自己常常忽略的社會角落,便從社會結構、社會動力和社會風情等幾個層面把握到了中國社會的整體狀況。
中國社會在數千年的發展歷程中,“革命”是一個不能忽略的重要方面。竹內實經過深入思索,認為中國有兩股勢力在實際上推動革命。一是由知識分子即精英們發動的革命,一是由民眾掀起的革命(通常即造反)。這兩種革命是相互糾纏在一起的。這確實是中國革命的一大特點。如果從盜跖算起,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莫不如此。竹內實的主要興趣是阿Q們站起來革命的情形。阿Q們當然是革命的追隨者,常常還成為革命的主力,然而當革命受挫,阿Q們常常又成為不為民眾理解的犧牲品。這是阿Q們的悲劇,何嘗又不是中國歷史上很多革命的悲劇?竹內實先生也注意到:一些知識分子如譚嗣同、章炳麟等,即使要想革命,也無法真正鬧起革命來。能夠使革命成功的,是一群具有使命感的知識分子團結廣大民眾一道奮斗。這樣的看法就比較接近毛澤東的意見了。
在追蹤中國現實發展的步履方面,處在同一時空中的竹內實可謂“亦步亦趨”。“文化大革命”剛爆發,他就密切關注其進行狀況。“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他又對毛澤東逝世后中國的走向、邁向“新長征”第一步的中國面臨的課題、中國的現代化趨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經濟狀況等,做了十分精當的分析。作者在真實地描述和客觀地評析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及其背景和原因的基礎上,對中國的進步和發展表示出了由衷的贊譽和堅定的信心,這也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縱觀中國社會的發展和演進,表面上似乎在不斷變化,王朝更迭、起義造反、革命改良等等,都在改變著中國社會的面貌乃至部分內部結構。但其實“變”中有許多是“不變”的。中國的城墻就是一例。記得中國著名作家陸文夫曾寫有一個中篇小說《圍墻》,大大小小的單位和部門都畫地為牢,實是中國一景。這種狀況直到改革開放后才有所改觀。而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城墻、圍墻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竹內實先生稱城墻為“城市包裹著柔軟肉體的硬殼”,是一個非常精到的比喻。他分析道:里三層、外三層般的城墻擋住外來者,而在里面的人們則可以在多重墻壁里安然酣睡。子子孫孫接連不斷地酣睡下去,就成了中華文明的酣睡了。于是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停滯。當然,竹內實先生還算辯證,承認這種停滯恰好也標志著中華文明的成熟。問題是,熟透了就會潰爛。所以,中華文明和中國社會一樣,也需要改革,也需要開放。這可比社會改革更為任重道遠。
探尋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和文化緣由
中國社會為什么這樣發展而不是另樣發展?為什么會發展成這樣而不是別樣?這是歷史演變的結果,也是傳統制約的結果。因此,竹內實先生在追蹤中國社會現實狀況之后,又將他睿智的眼光投向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
饒有趣味的是,竹內實先生通過對中國古都的游歷和探究,獲得了一個驚人的發現:中國古代主要王朝的長度具有一個共同點。西周、唐、宋、明、清這幾個重要王朝的長度無一不是300年。當然這是大約數,上述各朝中有的略長一點,有的略短一點。就是說,“一朝300年”意味著各王朝所具有的特定體制(包括政治、經濟、學術、社會結構之類的整個制度),都享有300年的壽命。這真是一個有意思的發現。
中華民族悠久的發展歷程,是那樣的紛繁復雜,讓后人和外人看了都覺得眼花繚亂。其實,這并非沒有軌跡可尋。竹內實由此試圖去探索中華思想中的基本價值觀,探尋古代思想的代表孔子及其《論語》,探討現代思想的代表毛澤東及其《矛盾論》。他還特別仔細地去分析了“兩與對”、“三與空(或虛)”這樣一些我們幾乎難于想到的問題。而正是在這類的問題里,恰好就隱藏著中華文化密碼的某些重要方面。他指出:中國人的世界觀認為,世界是由“兩”構成的,所以首先是把“兩”即二視為一個統一體,然后再將其分解為一加一。“一”是事物的不充足狀態,“奇數”是不同于世事之常態。“兩”有時可以與“對”相通。那“三”呢?竹內實先生認為:所謂“三”是無法維持陰陽的秩序時的產物,而那結果便意味著“萬物”,此乃“三生萬物”是也。至于“空”(或“虛”),與這神秘的“三”有著某種密切的聯系。只有深入到此處,才能“由一滴水見太陽”——由一些細微處去洞察中華民族的民族特性。
隔海相望帶來的模糊和隔閡
但竹內實先生畢竟是外國人,雖說他十分熱愛中國,可他的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與我們國內學者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一些看法不很準確,一些見解雖然新穎但不太深刻,有些說法甚至還有錯訛。對此我們也無需諱言。
竹內實先生對中國革命的分析很有見地,可是他追溯到最后,竟然認為:“發動革命的最初與最終的障礙是什么,那便是如何同孝的觀念進行斗爭”。“孝”自始至終是革命的主要障礙。這個看法比較新穎,這個結論也能為我們觀察革命現象時提供一個獨到的視角,但這樣的判斷卻是不準確的,也是比較淺顯的。革命的主要障礙還是要到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去尋找,而不是到每個個體的觀念中去尋找。說是由于“孝”的觀念,父母不會讓子女去革命或造反,可歷史上,父母和子女一同參加革命和造反的情況一點都不鮮見。
“一朝300年”,是竹內實先生的一個很獨到的發現。但他的解釋卻是歷史循環往復論,認為歷史的發展有既定的目標,這未免淪入歷史宿命論。歷史固然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和內在邏輯,但那是社會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且歷史的確是在不斷進步的,不管是波浪式前進還是螺旋式上升,都不可能是循環往復,不斷在一個封閉的圈子中旋轉的。
當然,我們不必苛求竹內實先生。只需指出他的錯訛和與我們的分歧即可。畢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給我們提供的啟發和思索,較這些不足和缺憾來說可是多得多了。
(編輯:高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