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文學:忠實與超越之美
電影×文學:忠實與超越之美
——影評家周黎明的“答疑解惑”

《白鹿原》是近年文學改編成電影的艱難嘗試

《安娜·卡列尼娜》已被無數次搬上銀幕,最近又被英國導演喬·懷特改編
電影能夠為文學帶來什么?
文學能夠為電影帶來什么?
文學與電影有天然的密切聯系——文學表達的是文字的、靜態的美;而電影是感官結合的體驗,動態的美。從《亂世佳人》《呼嘯山莊》《簡·愛》……到最近的《安娜·卡列尼娜》《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了不起的蓋茨比》,再到國內的《霸王別姬》《白鹿原》……電影創作離不開文學,電影也讓文字走得更遠。小說原著賦予了電影簡潔的故事框架、鮮明的主題和生動的人物形象;電影則將這些延伸成影像,滿足了人們的感官需求。被稱為“中國的羅杰·伊伯特”的著名影評人周黎明在日前的一次講座上,在對電影與文學的關系做了有趣的比較和案例分析后,更對當下影視業的現實問題做了頗有價值的解答。以下是其與聽眾問答的部分內容。

小說一直是電影改編的重要素材,根據美國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即將在中國上映
在中國,職業影評人不超過5個
問:在當下這個影像爆炸的時代,很多人習慣先通過文字了解一部電影,然后再用觀看這樣一種方式。那么是否可以探討一下,影評人在中國有沒有可能把它變成一個職業化的培養方式?中國影評人的生存狀態是怎樣的?
周黎明:首先,我想說在中國不要立志于當影評人,它的確不是個好職業,甚至稱不上是一個職業,嚴格地說中國沒有真正意義的職業影評人。職業影評人的首要標準就是必須要獨立,在西方,影評人絕對不會受雇于某個電影公司,不會說電影公司發紅包讓你說好話你就說好話,職業影評人受雇于媒體,影評人對它受雇的媒體以及媒體的讀者服務,完全是兩條線分開的。但是不幸的是,即便是在美國,原來有300個職業影評人,因為最近幾年紙媒的不景氣,有一半多都被解雇了,丟了“飯碗”。可以說真正意義上以寫影評維生的人是非常非常之少的,國內我能數得過來的相對職業的影評人絕不超過5個。
從另一個角度說,有一部分影評人寫影評,他是希望能夠進入影視這個行業,影評寫得好的影評人,自然對電影的欣賞能力和水平都是比較高的,再慢慢轉向創作,其實這中間是沒有鴻溝的。在美國這種情況比較少,但是在法國非常多,我們知道的幾乎所有法國“新浪潮”的創作主將都是寫影評的高手,是《電影手冊》這樣的獨立影評刊物培養出來的。當下由于影像技術更易于獲得,比如拍攝、剪輯原來都很昂貴,但是現在拿一部手機就可以拍出一部電影,在筆記本電腦上就可以剪輯完成,所以拍電影的門檻是大大降低。我是在想,無論是創作欲望來講,還是實際獲得的報酬,可以將寫影評作為一個起步,一個鍛煉,可以從寫劇本開始,而寫劇本的一批人當中很可能有一批人是可以當得了導演的,那么也就此可以發掘出潛力來。
我本人也不是以寫影評為生的,因為實在很難以此養家糊口,我有一份英文寫作的職業,因為那份職業使得我可以在寫影評的時候保持客觀和獨立。

以美劇《新聞編輯室》為代表的英美劇越來越具有文學價值
英劇美劇走向思想的縱深處
問:將影視改編成文學是否也是一個方向?另一個問題是,現在人們已經習慣用影像以及別人的經驗去了解這個世界,越往后這種趨勢越嚴重,比如以前的作家他都是自己去體驗生活,未來的作家會不會是通過電影去體驗別人的情感,去虛構和寫作?
周黎明:有不少影片如果故事是原創的話,會同期寫成一個小說,然后在影片上映時出版,通過電影宣傳的勢頭,也可以把小說熱銷出去。但是這樣的小說,基本上是沒有太多文學價值的。劉恒既寫電影劇本,也寫話劇劇本,他說過很有意思的一句話:我寫的話劇劇本每演一次是在給劇本增值,而電影劇本寫完之后拍成電影,就進入了墳墓,它的價值已經到此為止了。
第二個問題中提到的這個趨勢應當說是跟這個市場有關,比如你花一年、兩年寫出的一部小說非常幸運地被出版社選中出版了,一本也就獲得3000元至5000元的稿費。而如果寫成劇本能賣出去的話,就是幾十倍的價碼,電視劇會更高。在金錢面前,可以想見,大部分有些才華的人,會趨向于寫影視劇本,尤其是電視劇本。這個就是市場決定的,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去看書,覺得生活壓力很大,看書很累,因為文字是需要腦海里翻譯成影像的,這道工序是需要教育修養和理解力的,影視劇已經做好了影像翻譯這一個步驟,看一看既省力又過癮。在我看來現在中國大部分電視劇是沒有太多營養的,只是一個消磨時間的手段。我認為,作為一個年輕人,在文藝方面有所追求的話,你就應該抽出一定的時間貢獻給文字,因為文字的美妙是影像絕不會取代的,正因為文字需要翻譯,會在腦海里暢游形成一種想象,而這就是對你想象力、創造力的考驗與鍛煉,鍛煉得多了,文字的創造力就會強化。我們的這個時代,隨處可見的手機視頻拍攝,人人都可以成為記者,甚至是導演,相信在未來的十年內,這種趨勢會更加強化,但是文字是無法取代的。
有一個火種,在我看來可以給寫影視劇的人以希望,也就是美劇和英劇。近十年來,美劇和英劇越來越具有文學價值,它不再是面對普通大眾的一個載體,逐漸變成了一個面向精英的載體,也就是從人物的塑造以及思想性的挖掘方面,不斷的提高,獲得了以前的電視劇完全望塵莫及的高度,甚至從某種程度看它超越了電影。最近大家流行看美劇、英劇,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它所呈現的深度實際上是嫁接了文字和影像。像《新聞編輯室》和《白宮群英》的編劇艾倫·索金,絕對是頂尖的戲劇編劇。

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近年大獲成功的根據文學改編的作品
李安也會輸給《小時代》
問:我妹妹上初中,她對《小時代》喜愛得不得了,而我對這部片有極不同的看法,不知怎么跟她溝通,想從您這里獲得答案。您對當下中國電影的現狀有什么看法?
周黎明:先說我對中國電影當下的看法,在我看來這兩年中國電影是走上了一個良好的軌道。這個軌道就是類型化,從《失戀33天》開始。中國的電影界從這部片開始意識到中國式大片,尤其是古裝大片,有可能是一條死胡同。從2002年《英雄》開始,中國電影走了將近10年的大片路線,這里面有兩層原因,其一:是希望能夠與好萊塢大片抗衡;其二:盜版,這個說得比較少,因為大片的視聽效果更能吸引觀眾去影院體驗身臨其境的感受。去年的《泰囧》到今年的《北京遇上西雅圖》《致青春》《中國合伙人》都是“走”的類型片套路,這些影片從思想藝術性來講沒有那么高,首先源于追求沒有那么高,沒有說我就非要做一部傳世的作品,只是做一部讓觀眾有共鳴,或者感到過癮的作品。現在我們知道,對抗好萊塢得有拳頭產品,這個產品不是中國式大片一條路,或者只拼兩三個導演,而是需要一大批的導演,50個甚至是100個能夠拍類型片的導演。像徐錚、薛曉璐這樣一批導演,他們對類型片是由衷地接受的,他們找到了一個平衡點。
但現在有一個問題,值得探討。類型片有不少像《泰囧》《北京遇上西雅圖》這樣稱職的,也有一些從技術、敘事、更不用說思想性上并不稱職的類型片,卻獲得了巨大的票房,包括美國的《暮光之城》系列賣得非常好,但是年年得“金酸梅”獎,作為商品它是成功的,但是作為文藝作品它是不合格的。從段位上來講,李安作品的段位高得很,但是如果李安的作品碰上今年暑期檔,它在市場上也會輸給《小時代》,這個就是現實。“粉絲電影”完全可以做得更努力、更好,對青年一代有很好的影響,比如好萊塢大片,有不少影片的定位就是13歲男孩,但是投資方、創作者都會花盡心思想把這一部拍得如何更好一點。與此同時,投資方和創作者心里都很明白,這部片就是讓觀眾開心開心、然后片方賺些錢,他們不會拿這個作品跟《教父》去比。所以,我們的投資方應該也兩條腿走路,比如好萊塢的片方夏天商業片賺錢了,就會想要在冬天賺名聲,要投資一些真正有藝術價值的片子。我認識一個中國投資方,他投的一部片賺了很多,但他一直耿耿于懷地跟我說很后悔之前投錢拍了一部獲得過金馬獎的藝術影片,這部影片投資成本只有500萬元人民幣。這就是中國的現實,看到的就是利益最大化,回報最大化,雖然已經賺了很多錢仍然會覺得投不賺錢的藝術片是一件極為失敗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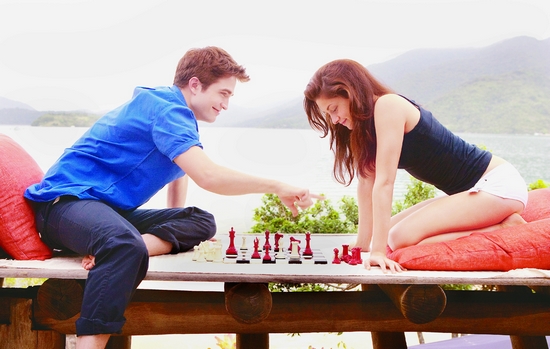
電影《暮光之城》根據同名小說改編,頗受年輕觀眾歡迎
【鏈接】
周黎明(Raymond Zhou),雙語作家、文化評論人、影評人,畢業于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獲MBA學位。常年為中英文報刊撰寫專欄,包括《看電影》《中國日報》《名Famous》等。每年撰寫并發表中英文文章各百余篇,已出版《2008中國時評年選》《你的,大大的壞:遠離標準答案的影評》《影君子》等18種著作,其中英文著作三種。每年參與電視及網絡訪談節目百多個,以及各種論壇、電影節、電視節目及其他文藝領域的座談和咨詢,擔任嘉賓、策劃或主持。評論的題目涉及電影、電視、戲劇、古典音樂、文學及社會文化,尤以跨越中西文化的內容見長。被《洛杉磯時報》(2012年3月10日)稱為“中國的羅杰·伊伯特”。
(編輯: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