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奴”樊建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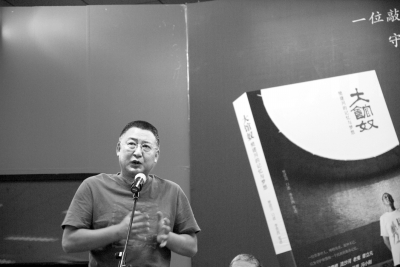
樊建川的頭銜有點兒“雜”,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秘書長、四川省收藏家協會副主席、建川實業集團董事長、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的經歷有點兒“怪”,從軍校轉業,到宜賓市的副市長,轉身下海,成為房地產開發商。
更怪的是,這位開發商最熱衷的事業,不是建商品房,而是建博物館。社會上有“房奴”“車奴”,樊建川自稱“館奴”,而且是“大館奴”。
日前,在《大館奴》新書發布會現場,樊建川的角色又一次發生變化。此刻,他是一位講述者,講述他的書和他的夢——都與博物館有關。
與他這個人一樣,樊建川的收藏也稱得上“另類”,有八路軍用過的子彈帶,有華僑捐助抗日的支票,有印著“抓革命、促生產”的“文革”搪瓷水杯,也有汶川地震時“可樂男孩”薛梟喝的那個可樂罐。
“別人收藏唐宋元明清,收藏梅蘭竹菊、才子佳人,我收藏的大多是些火爆爆的東西。”樊建川說。在四川大邑的建川博物館群落,已經建成了30多個主題博物館,大多與抗戰、“文革”、知青、災難有關。在樊建川看來,收藏戰爭是為了留住和平,收藏教訓是為了美好的未來,收藏災難是為了長久的安寧,“我是想保留一些歷史的細節。時間將證明,這些藏品對我們的國家、社會肯定是有用的,是更有價值的藏品。”
樊建川對抗戰文物有著特殊的情結:“日本總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承認侵華歷史,甚至篡改歷史,為戰爭罪人鳴冤招魂。我們既要理直氣壯地駁斥否認侵華罪行的言論,更應該把事實擺出來,文物就是最好的證據。”
2000年7月,樊建川聽說一批日軍投降時交出的系列機密公文即將拍賣,有海外商人已籌足資金準備“豪奪”。他擔心自己的資金無法與之匹敵,就開始四處打探這批拍品的來源,希望說服賣家撤拍。在拍賣會開始的前一天,樊建川找到了這位賣家,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最終賣家同意撤拍,直接將拍品賣給樊建川。能把這批日軍侵華的罪證留在中國,留在中國人手中,樊建川很欣慰。
“建川博物館的未來應歸于國家。我和妻子已經商定并立下遺囑,當我們不在的時候,將建川博物館和安仁文化公司的全部股權,捐贈給成都市人民政府。唯有這樣,博物館才能長存,這些文物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份收在《大館奴》中的《遺贈書》,落款是樊建川。
詩人流沙河這樣評價樊建川:“看他辦博物館立志救世,‘為人太多,自為太少’,很像《莊子》書中的尹文子。至于粗茶淡飯,布服素衣,‘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又很像墨子。”
然而,樊建川并未以古人自況,他想做的,無非是一個“敲鐘人”,為忙碌奔波的人們敲響警鐘。“我不希望參觀者像游客一樣,在匆忙之間,花很少時間來看我的博物館。我希望一部分人來看,看了以后有五分鐘的思考,在生活的路上停下五分鐘,回頭看看,把人生的意義搞得清楚一點。”電影導演陸川,就在建川博物館停下了腳步。拍攝《南京!南京!》時,陸川曾和同事吃住在建川博物館:“在建川博物館,我對歷史的感受、判斷,發生了很大變化。”
“敲鐘人”樊建川有一個夢想——憑他一個人的力量建100個博物館,做一個真真正正的“大館奴”。
(編輯:高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