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取中國的獨(dú)特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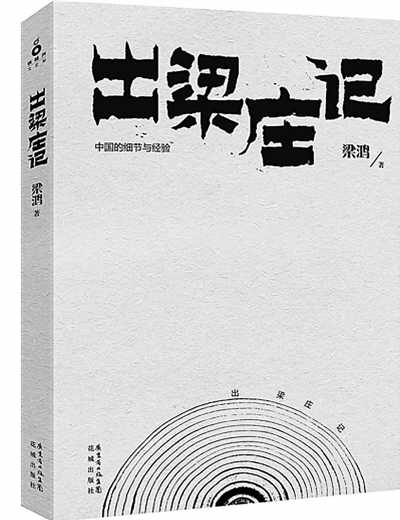
《出梁莊記》:梁鴻著,花城出版社出版。
憑借《中國在梁莊》以及新近出版的《出梁莊記》,作家梁鴻讓很多讀者記住了中原農(nóng)村的一個(gè)小小村莊。“梁莊”,成了近年來突然出現(xiàn)在中國文壇的一個(gè)“意象”。這是梁鴻自己努力的結(jié)果,但我更愿意將其理解為萬千中國鄉(xiāng)村中的“一個(gè)”,因其普遍性而成為典型,因其相似性而被人感知,因其真實(shí)性而被看作“代表”。
《出梁莊記》真正寫到了“中國”,因?yàn)闀械牧呵f人幾乎遍布中國大江南北,可以說,這也是看取中國的一個(gè)獨(dú)特窗口。今日中國就像一個(gè)變化無窮的萬花筒,我們可以從一百個(gè)方向看中國,每個(gè)人看到的都不一樣,看完了都有描述、評價(jià)的沖動(dòng),所有的描述和評價(jià)在同樣看過這個(gè)萬花筒的人來說,都是未曾見到卻又似曾相識的。而且,每一個(gè)觀看者的態(tài)度,歌贊、批判,興奮、憤懣,美化、丑化,都有充分的理由,都給人可信的感覺,這些景象和情緒,它們相互矛盾甚至沖突,相互背反甚至分裂,質(zhì)地完全不同,情狀和面貌相差太遠(yuǎn)以至于難以貼合到一個(gè)版圖上。然而,這卻是今日中國必須面對的實(shí)情。
中國的發(fā)展迅猛異常,在這突飛猛進(jìn)的過程中,也有很多掉隊(duì)者、被甩下者、沒有能力搭車前行者。巨變中的那些不變其實(shí)也一樣發(fā)生著裂變,不過因?yàn)樗鼈兯坪醪淮須v史前行的方向和主流,所以很少為人關(guān)注。但或許若干年后,人們才會意識到,他們才是最廣大、最普遍、最具歷史影響力的大多數(shù)。就像魯迅那樣,在別人寫革命、寫進(jìn)步的時(shí)候,他卻表現(xiàn)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農(nóng)民以及處在歷史夾縫中的灰色的小知識分子。他從沉默者和被淘汰的多余者身上,思考中國的歷史、現(xiàn)在與未來。
《出梁莊記》里,我們看到的一切足夠觸目驚心。由于中國社會階層的分化,讓一個(gè)看上去跟時(shí)代前行的步伐完全無關(guān)的中原村莊,卻一樣被裹挾在其中無法保持平靜。同一個(gè)村莊的人,有失去土地的流浪者,有外出打工的求生者,以及無一技之長的遠(yuǎn)行者。他們大多數(shù)人處境艱難,他們其實(shí)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怎樣,但為了自己和親人,為了改變和不屈服,恍惚間踏上外出的道路。這就是真實(shí)中國的一部分,它可能不入新聞人的鏡頭,不能搬上舞臺,也少有被文人雅士們夸贊“無憂無慮真是田家樂”的機(jī)會,但它們的真實(shí)性本身,就足以超越任何贊頌與批判。
我想到梁鴻寫作的身份問題。其實(shí),梁鴻本人也應(yīng)當(dāng)是“出梁莊”者中的一分子。當(dāng)代中國農(nóng)村青年的出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兩種:靠學(xué)習(xí)和智慧考上大學(xué)、改變命運(yùn)的幸運(yùn)者,沒有能力和機(jī)會獲得那種幸運(yùn)的更多數(shù)的青年。前者如梁鴻,可以“出梁莊”而入京城,成了博士、教授,而更多的梁莊青年,如她兒時(shí)最好的玩伴堂弟“小柱”,卻只能東闖西撞地去打工養(yǎng)活自己。梁鴻和小柱之間的差距,就是短短的20多年里,同樣背景、同樣出身的中國人身上產(chǎn)生的巨大反差。中國社會的很多悲喜,很多戲劇性與荒誕感,都是這種迅速變化造成的。
通讀全書可以發(fā)現(xiàn),梁鴻盡量不去參與而只是聆聽,內(nèi)心無距離,筆下盡力保持克制。她是同鄉(xiāng),所以沒有感情障礙;她又是“他者”,因?yàn)樗呀?jīng)抽離出來,命運(yùn)不受梁莊人命運(yùn)趨勢的擺布。其實(shí),至少在這本《出梁莊記》里,梁鴻還應(yīng)當(dāng)讓自己融入其中,成為對話者、參與者。因?yàn)椤俺隽呵f”本身是一個(gè)物理位移,命運(yùn)交錯(cuò)是另一話題。如果那樣,本書的意味會更深長。至少,梁鴻和小柱之間的巨大反差,讓我想起魯迅的《故鄉(xiāng)》。“我”因閏土的一聲“老爺”而心驚,于是提出“希望”——閏土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能不再隔膜。而魯迅的理想,到梁莊這里還遠(yuǎn)未實(shí)現(xiàn),在我們很多人的周圍也沒有完全成為現(xiàn)實(shí)。如果書中能把作者本人與村民們的對話也呈現(xiàn)出來,那不但更有現(xiàn)場感,而且更能闡釋“中國”的分量。
(編輯:高晴)
| · | 梁鴻等獲首屆非虛構(gòu)寫作大獎(jiǎ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