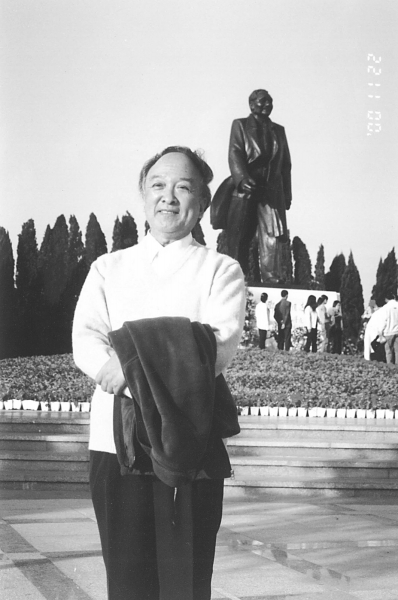中關園上課
先生給我們上的文藝美學專題選修課,不是在教學樓,也不是在中文系所在的五院,而是在中關園一公寓他家里。我們文藝學專業文藝美學方向總共三個同學,分別來自北京、上海和四川,可謂來自天南海北。我們到先生家里,總會有綠茶一杯,有時還有師母做的美味。先生侃侃而談,就文藝美學的前沿問題提出他的見解。對我們的提問,先生總是循循善誘,及時作答,中間還穿插他多年來的治學體會。先生在這種“小班研討課”上留給我的東西是永難忘懷的:一是說搞文藝理論、文藝美學的人,要始終保持一種開放的、包容的心態,不能封閉和保守(而那時保守勢力還很頑固);二是藝術不是現實生活的一般反映的產物,而是審美體驗的結晶(這種觀點那時曾引起保守勢力的壓制);三是搞理論的要懂藝術特性,更要善于舉例。例子好不好,關系到你的理論是否站得住腳。不能舉出恰當的例子,說明你的理論本身有問題。這些都成為我后來治學的座右銘。
這樣上課給人真正的登堂入室的感覺。下課后回到宿舍談起時,同屋其他專業的研究生同學都羨慕不已。等到多年后我自己帶研究生時,每個專業招生人數逐漸增加,導師也多了起來,這種上課方式就再也沒實行過。因此,這種特殊的北大上課感覺,自然就成了我心中永遠的回憶了。
沿灑登黃山
上研究生二年級時,我們三名碩士生跟隨先生到南方實習,先生親自給取的題目就是“藝術美與自然美的比較研究”。多年后想起來,仍然覺得這個題目堪稱妙絕:既游山玩水,又符合學科專業培養需要!記得先生帶我們去的第一站就是黃山。我們先坐車到后山,從云谷寺上山。先生穿著一雙拖鞋,在彎彎山道中瀟灑自在地行走,宛若魏晉風度再現。這樣的情景在我的腦海里永久地定格下來。
先生的育人方式,是開放式和啟發式的,就是不斷給你一些啟示,更多地讓你自己去領會、摸索和思考。關鍵是看你自己能否時時做到又學又問。現在想來,那時愚鈍的我問得太少了,真是慚愧和后悔,想必遠不如后來的學弟學妹們得的真傳多。
不停的開拓者
先生治學,給我的突出印象是開拓。進入新時期以來,他青春煥發,昂揚進取,永不停頓地在開拓,開拓,幾乎沒有停留的時候。我想至少在這么四個學術領域,他都曾先后成為全國學界的開路先鋒和引領者:一是當我們初次接觸美學時,他創立了文藝美學,被譽為中國大陸文藝美學學科的“教父”;二是當我們剛剛試圖跟上他的文藝美學腳步時,他已經在著手西方文論教材的拓荒行動了;三是隨后他又毅然離開北大南下深圳,在新興的比較文學中倡導比較詩學研究,將比較文學引領到理論反思的高度;四是再后來,他倡導文化美學研究,一方面是讓美學從高雅文化拓展到大眾文化,另一方面是把商業性和消費性愈來愈濃的當代審美文化潮流提升到美學理論高度去把握。一個學者一生能做的事情實在有限,能有一項開拓之功屬于自己,已很了得,更何況這么多呢!
外柔內剛的詩人美學家
先生既是典型的學者,又是詩人,同時還擔任過系主任、學會會長。在他身上,既有江南人的敏感、柔婉和細膩,還有詩人的浪漫和詩情,也有北大學者的耿介、正直。可以說,先生是外柔而又內剛的人,或是柔婉而又剛硬的人。說到柔婉,我沒有見過先生激動地大聲斥責任何人,甚至連語氣重的話也沒聽到過,當然就絕對聽不到罵人的話了。他總是那么文質彬彬,那么溫和謙讓。但同時,我又見到,當先生毅然選擇南下時,曾是那么果斷、決絕,那么義無反顧。在他的身上,我見證了一位敏感、柔婉而耿直的浪漫詩人,或者更準確地說,一位外柔內剛的詩人美學家。
多元學緣人與耿介之氣
先生的這種特殊的學術稟賦,我想是同他的個人氣質和多元學緣氛圍有關的。他在青年和成年時期,受到中國現代革命的浪漫詩情與跨學校和多學緣的相互激蕩和持續涵濡。1952年院系調整時,來自北京大學的游國恩教授,清華大學的俞平伯教授、季鎮淮教授和王瑤教授,燕京大學的林庚教授和吳組緗教授,中山大學的王力教授,以及來自南方的楊晦教授等,一時間,國內中文領域頂尖人才悉數薈萃燕園。先生就是在這樣的多元學緣氛圍中進入北大求學并隨后留校執教的。那時的北大中文系教師中,回蕩著一種多元學緣激蕩下及開放時代環境中知識分子的耿介之氣。每遇不平之事,總會直率表達,甚至會選擇瀟灑地離開。富有才華的黃修己先生等以及其他系的知名教師,都先后以這樣的名士風度留在了北大人的記憶里。
南下傳遞人
先生南下,看起來似乎只是他個人的人生選擇。這樣理解當然沒有任何問題。但在我看來,這種個人選擇的深層,應該隱伏著歷史老人的老謀深算和先生個人的自覺信奉及踐行。那次院系調整時,國家曾以行政抽取和集聚手段,將首都地區高校的全部乃至全國高校的部分文科精華薈萃于北大一校之中,造成了北大文科過于壟斷的學科權力格局,也就形成了北大文科在全國的“巨無霸”地位和超強的學科權力壟斷。而后來,當歷史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為了糾正這種學術資源分配不公平的錯誤,給全國高校以同樣的發展機遇,歷史老人又著手把薈萃于北大的文科精華,部分地還給全國學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以北大文科精華反過來重新回饋給全國。先生正是適時地、自覺地成為這筆歷史宿債的償還者,或者說,成為改革開放時代全國學術前沿精華的南下傳遞人。原來,先生在近30年前選擇南下,說到底,是在自覺地和實際地履行一名北大人的天職:把未名湖畔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學術火種播撒到南國最邊緣的深圳灣。當時地處全國改革開放前哨深圳的新興大學深圳大學,確實充滿宏大的改革理想,被視為全國高校改革的最前沿,凝聚著全國高教界的改革愿景,而懷揣如此神圣使命南下深圳大學的,除先生之外,還有北大和清華的不少知名學者及校領導,如北大的湯一介教授和樂黛云教授夫婦、李賦寧教授,清華的副校長張維教授,以及那時正充滿學術抱負的應屆畢業碩士生、青年美學家劉小楓,還有后來接替先生出任深圳大學中文系主任并一直做到校長的、我的碩士同級學兄章必功等。如今,深圳灣早已不再是文化的邊緣地帶,而是學術開放和文化變革的前沿陣地了。此時,杖朝之年仍堅持在碧波中揮臂擊水的胡經之先生,該舒心地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