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武談《哈扎爾辭典》:作者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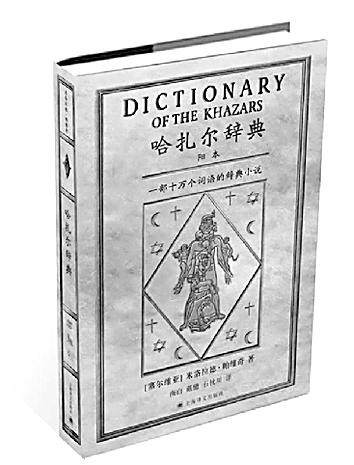
《哈扎爾辭典》
【塞爾維亞】 米洛拉德·帕維奇 著
南山 戴驄 石枕川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米洛拉德·帕維奇(1929-2009)
塞爾維亞作家,文藝學(xué)家,哲學(xué)博士,貝爾格萊德大學(xué)教授,塞爾維亞科學(xué)和藝術(shù)院院士,全歐文化學(xué)會(huì)和全歐科學(xué)與藝術(shù)家協(xié)會(huì)成員。曾被美國(guó)、歐洲和巴西的學(xué)者提名為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候選人。
哈扎爾是一個(gè)存在于拜占庭時(shí)代的王國(guó),《哈扎爾辭典》一直記錄這個(gè)曾經(jīng)存在后又沒(méi)落的王國(guó)的歷史。這部《哈扎爾辭典》分為紅書(shū)(基督教)、綠書(shū)(伊斯蘭教)和黃書(shū)(猶太教)三部分,綜合了這三種宗教各自記錄下來(lái)的史實(shí),并是以辭典的形式記錄的。它不用時(shí)序處理,而是按字母的次序來(lái)記錄。此書(shū)中的人物不停地轉(zhuǎn)世,或者是來(lái)回時(shí)空的旅程,在一段三個(gè)人的關(guān)系里,兩個(gè)人互相“托夢(mèng)”,透過(guò)夢(mèng)境,這些人穿梭時(shí)空。
17年前,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副教授張頤武,因《哈扎爾辭典》惹出了一場(chǎng)官司。17年后,張頤武教授說(shuō),現(xiàn)在的自己會(huì)更加寬容。
15年前,30多歲的讀者止庵,對(duì)《哈扎爾辭典》的興趣在于其寫(xiě)作方法的獨(dú)特。15年后,50多歲的書(shū)評(píng)人止庵重讀《哈扎爾辭典》,從中發(fā)現(xiàn)的是文明的沖突。
日前,藉由《哈扎爾辭典》新版面世的機(jī)會(huì),張頤武和止庵坐到一起,談米洛拉德·帕維奇和他的《哈扎爾辭典》,談文學(xué)與想象,談閱讀與人生。
他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世界
張頤武:1994年,我在《外國(guó)文藝》雜志上看到南山、戴驄、石枕川三位先生翻譯的《哈扎爾辭典》。盡管那時(shí)發(fā)表的還不是全本,但我覺(jué)得這本書(shū)的想象力、創(chuàng)造力非比尋常。作者重新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世界——“哈扎爾國(guó)王”,這說(shuō)明文學(xué)有無(wú)限的可能性。
止庵:歷史上確實(shí)有哈扎爾王國(guó),有哈扎爾人,但史實(shí)不是特別清楚。《哈扎爾辭典》完全制造出一個(gè)世界,跟歷史上有沒(méi)有哈扎爾無(wú)關(guān)。這本書(shū)中的三部辭典紅書(shū)、綠書(shū)、黃書(shū)分別代表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其實(shí)是不同宗教背景下的辭典。三部辭典有好多詞條是一樣的,但敘述的角度不同,解釋就完全不一樣,文化的沖突存于其中。而恰恰就是這三種文化的沖突,導(dǎo)致了哈扎爾王國(guó)的滅亡。
張頤武:《哈扎爾辭典》既是一個(gè)從零點(diǎn)起跳,作家想象的結(jié)晶,也有豐厚的歷史知識(shí)作為背景。帕維奇穿梭于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之間,展示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讀這本書(shū),你可以隨機(jī)翻開(kāi)一頁(yè),從這個(gè)詞看到另外一個(gè)詞,不斷地牽連到很多詞,引你進(jìn)到這個(gè)文化的不同側(cè)面,就跟看辭典一樣。
想象是一種能力
止庵:想象是一種能力。這種能力可以細(xì)分為兩種:一種是對(duì)曾經(jīng)有過(guò)的真實(shí)的彌補(bǔ)。比如拍古代題材的電視劇,就要?jiǎng)佑孟胂罅ο牍糯嗽趺凑f(shuō)話;還有一種想象力,是創(chuàng)造的想象力,完全跟現(xiàn)實(shí)沒(méi)關(guān)系,《哈扎爾辭典》就屬于這種。假如現(xiàn)在這個(gè)世界是一個(gè)世界,在帕維奇書(shū)里面出現(xiàn)另外一個(gè)世界,跟我們這個(gè)世界是同等的關(guān)系。我們必須承認(rèn),人類(lèi)有這么一種能力,在現(xiàn)在的生活之外,又做出一個(gè)東西,使得我們這個(gè)世界更大。
上世紀(jì)80年代初,帕維奇寫(xiě)《哈扎爾辭典》時(shí),已經(jīng)50多歲了。可以說(shuō),《哈扎爾辭典》是一本關(guān)于人類(lèi)如何挑戰(zhàn)智力極限的書(shū),完全是智力的產(chǎn)物。就像百米賽跑,很早的時(shí)候,世界紀(jì)錄是11秒,60年前是10秒,現(xiàn)在是9秒多。人類(lèi)有一個(gè)極限,大家不斷地去接近極限。《哈扎爾辭典》跟其他書(shū)的區(qū)別就是在創(chuàng)造的路上走得最遠(yuǎn)。沿著《哈扎爾辭典》往前說(shuō),還有博爾赫斯、卡爾維諾等若干作家,他們是一路人,他們共同把我們的世界變大。
張頤武:《哈扎爾辭典》的開(kāi)放性、多元化,是后現(xiàn)代文化一個(gè)最大的特色。現(xiàn)代性的特點(diǎn)是宏大敘事,有開(kāi)頭,有結(jié)尾,很完整。后現(xiàn)代就是開(kāi)放多元,糊里糊涂,但是糊里糊涂中有獨(dú)特的力量。我們普通人想象中的哈扎爾,一定跟古羅馬帝國(guó)一樣,有凱撒那樣的首領(lǐng),干了很多大事,經(jīng)歷很多斗爭(zhēng),這些具有戲劇性的東西。但帕維奇筆下的哈扎爾文明,寥寥幾筆,就毀滅了,完了就完了,沒(méi)那么多慘烈的故事。你會(huì)突然感到失落。
《哈扎爾辭典》有陰本、陽(yáng)本兩種版本,在中譯本中有11行的差別。差了這十幾行以后,讀者會(huì)發(fā)現(xiàn)這兩本書(shū)完全不同。為什么會(huì)有這種區(qū)別?我想到博爾赫斯的一篇小說(shuō),說(shuō)的是有一個(gè)人準(zhǔn)備重新寫(xiě)一本《堂吉訶德》。他寫(xiě)《堂吉訶德》,不是重編一本戲說(shuō)或后傳,而是一字一句都跟《堂吉訶德》一模一樣。由于他與塞萬(wàn)提斯生活的時(shí)空不同,塞萬(wàn)提斯是生活在十六七世紀(jì)的西班牙人,他是20世紀(jì)生活在拉丁美洲的一個(gè)人。雖然兩部書(shū)每字每句都一樣,但是意義卻完全不一樣。當(dāng)時(shí),我很震撼,這不是照抄嗎?但是這兩本書(shū)還真有不同。這本新的《堂吉訶德》,每一句的意義都與原作不一樣。《哈扎爾辭典》的陰本、陽(yáng)本,就像重寫(xiě)《堂吉訶德》一樣,是一種創(chuàng)造。
關(guān)于有用和無(wú)用
止庵:有人可能會(huì)問(wèn),我看清朝的電視劇,好歹知道清朝什么樣,從《哈扎爾辭典》中,能讀到些什么呢?這牽扯到一個(gè)很重要的觀點(diǎn):想象就是一個(gè)獨(dú)立的存在,它有自己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力是不能模仿的,存在就是價(jià)值。我們應(yīng)該從這個(gè)角度估量《哈扎爾辭典》的價(jià)值。
張頤武:清人說(shuō)過(guò)一句話,“不為無(wú)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人除了吃飽、吃好之外,還有一些不同的追求,這些追求使我們的生命有一些不同的意義。大家吃夠了紅燒肉,看夠了電視劇,讀《哈扎爾辭典》,好像是品嘗到了清粥小菜,讓你發(fā)現(xiàn)人生還可以有另外的選擇。
我從來(lái)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帕維奇,但是我覺(jué)得好像我的生命跟他生命的一部分息息相關(guān)。2009年,聽(tīng)到他故去的消息,我真的是覺(jué)得我生命的一部分離我而去了,我開(kāi)始老去了。
中文版《哈扎爾辭典》準(zhǔn)備再版時(shí),出版社提出用我的文章作前言,這其實(shí)是不合適的。我的文章,不應(yīng)該放在這么偉大的書(shū)的前面。但是我有一點(diǎn)坦然,就是我與這部書(shū)的因緣。把我的文章作為前言,可以說(shuō)明,一個(gè)講故事的人,他的故事會(huì)穿越時(shí)空,出現(xiàn)很多奇觀。(杜羽整理)
(編輯:曉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