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國文學三大新現象—— 淺俗化、小說失衡、青春雜志異軍突起
6月2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召開了“《中國文情報告》(2011~2012)發布會暨專家研討會”,謝壽先、陸建德、雷達、梁鴻鷹、彭學明、吳義勤、孟繁華、張志忠、解璽璋等專家參加了會議。
文學藍皮書共22萬字,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結集出版。它是2011年文學概述和大事記,是“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白燁帶領10多名成員作為學術課題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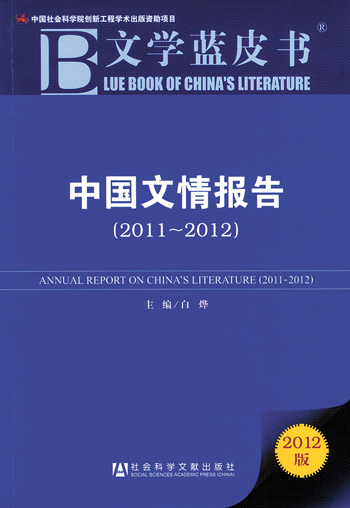
《中國文情報告》 白燁主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文學走向“淺俗化”
2011年是一十年代的第一年,這本文學藍皮書道出了這一年乃至這幾年一個重要的文學社會現象,即:文學閱讀的淺俗化。而文學閱讀的淺俗化,直接導致“文學的淺俗化”。
此次發布的《中國文情報告》說,過去,我們在對文學與藝術的認知與理解中,更多地強調文學的教育、認識與審美功用,也就是“文以載道”、“文以傳美”思想,而對文學還應該有的休閑、宣泄與娛樂的功用認識不足,甚至有所忽略。但這些年似乎又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那就是把輕松化、娛樂化日漸抬到至高無上的地步,矯枉過正了。
課題專家們認為,文學的淺俗化,與整個社會文化的淺俗化息息相關——各類電視節目都極力追求娛樂化、游戲性;學者的學術講壇被打造成變相的評書連播,或歷史故事的噱頭操作;交友相親節目被編制成寫真方式和娛樂性質的“美女秀”電視連續劇;報紙與網絡傳媒因為追求“娛樂至上”,演藝明星成為各種話題的重要主角,他們的各種八卦消息都會成為充斥版面與占據首頁的新聞與要聞。在以“找樂”的方式媚俗的世風影響之下,文學的閱讀也向淺俗的方向一路滑去,其中最為典型的表現,便是那些缺少人間氣息與人性溫度的玄幻與仙俠、驚悚與懸疑類文學作品在網際與紙媒都大行其道,不僅擁有越來越多的青少年讀者,而且為文藝生產的各個環節所看重,容易發表(特別是網站)和出版,容易被改編成影視、動漫、游戲等形式的延伸產品,以“全媒體”的方式廣為流傳。而正在成長的青少年讀者,因為感性大于理性,好奇又缺乏辨識力,不僅習慣于視屏閱讀、圖像閱讀,而且追求輕松閱讀、快餐閱讀,對青春成長和人生成熟更有價值和意義的紙質閱讀、深度閱讀反倒被當做過時的老朽傳統,被忽而略之,甚至棄之不顧了。這種閱讀取向,這種受眾構成,再反過來影響文學生產,會使傳統文化與經典文學的生存更為萎縮,發展更為艱難。
文學藍皮書認為,文學閱讀看起來是文學傳播之中的一個環節,但其實是文學生產的終端所在。而閱讀本身,內含了接受、學習與教育的多種功能與多重意蘊,如果文學生產的這個終端是淺俗化的,那就使文學生產的意義大打了折扣,并在受眾層次與文化情趣諸方面給未來的文學發展構成嚴重的限制和無形的障礙。因此,文學閱讀的問題,既關乎文學生產,又關乎文學大局,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視,并想方設法來解決。
小說失衡:長篇小說太盛行,中短篇小說受冷落
“在小說創作領域里,長篇小說從過去的年產2000多部,猛增到2011年年產4000部左右,而且以接連不斷的研討會、暢銷書排行榜等方式,在文學領域一家獨大,在文壇的影響如日中天……而且在數量增長的同時,質量也在不斷地提升。”白燁在《中國文情報告》的總報告里這樣寫道,“與此成反比的,是中短篇小說的寫作頗顯冷寂,生產趨于萎縮。這種不夠景氣的情形,既表現在有志于中短篇小說寫作的作者為數不多,后繼者為數寥寥,又表現在發表中短篇小說主要陣地,已退縮到體制內所主辦的數量不多影響也有限的傳統文學期刊,在當下影響巨大的網絡文學與文學出版中,或者沒有立足之地,或者不在視野之內,基本上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
這個失衡的小說怪現象,記者最早是在去年春天參加“丹霞杯”全球華文大賽頒獎會上聽說的,有一位曾獲得茅盾文學獎提名的小說家談到文學集子出版之事時說,中短篇小說、散文、詩歌出集子比較困難,而長篇小說出版則很容易。寫中短篇小說的優秀小說家缺乏,文學期刊最缺的是中短篇小說,尤其是好短篇。
近年來,長篇小說受到厚愛——不僅如此,甚至連報告文學、紀實文學,都是長篇的更受歡迎,而中短篇小說——甚至是中短篇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等出版集子都十分困難。
歷史上,我們有可以稱之為“偉大”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悲慘世界》《紅樓夢》《三國演義》,也一樣有可以稱之為“偉大”的短篇小說家莫泊桑、歐·亨利、博爾·郝斯、卡夫卡、蒲松齡等,寫出了許多流傳千古的名篇。
文學藍皮書對這一不正常的現象做出了如下描述:“有些小說家只以長篇小說為寫作目標,更有快槍手幾乎一年推出一部,人到中年就已經長篇等身了。”
書中分析原因認為:一是網絡小說通過炒作長篇小說,引起刺激,不斷連載,吸引讀者不斷閱讀,擴大網站影響力;二是出版社覺得長篇小說能夠通過版權經營、改編成影視劇進行延伸性經營,可以取得一連串經濟效益,而中短篇小說比較難做到。
這是商業利益所驅。除此之外,還有其它三方面原因:一是中短篇小說選集,各出版社可以不斷交叉遴選、不斷出版,版權的唯一性難控,難以帶來再版的滾動利潤;二是現代讀者心理,追求個人的自我獨立,喜歡繁華紛擾,不喜歡簡約凝練,獨立、完整又繁華紛擾的長篇小說切合了這種心態,討讀者歡迎;三是文學商業炒作——包括作品研討會、評論文章、媒體消息等,也偏重長篇小說,冷落中短篇小說。
物極必反。也許還沒有到過分極端的那一天,一旦到了那一天,一切就會反過來。
青春雜志書異軍突起
雜志與書的合一,也是近年中國的一個特殊文學現象。白燁在此書的總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青年作家主辦雜志書的勢頭不減,是青春文學領域里另一個新的增長點。”
2011年以前,雜志書已經出現,那是一種用書號不定期出雜志的一種邊緣做法。
“雜志書”即將雜志和書籍合在一起,成為獨具魅力的“雜志書”。它是日本創造推廣的一種新文化商品,文字少圖片多,雜志以書的形式發表,沒有雜志的時間限制,一般一本書就是一個專題。
但到了中國后,雜志書的內涵和外延又有了一些變化。
隨著一大批青春文學作家的不斷涉足和花樣翻新,以主編個性為風格,以作家粉絲為主要讀者群的青春文學雜志書聲名鵲起,除了前幾年異軍突起的郭敬明的《最小說》、饒雪漫的《最女性》、張悅然的《鯉》、蔡駿的《懸疑志》、郭妮的《火星少女》之外,在2011年,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了分別由著名青春文學作家笛安和落落主編的文學雜志《文藝風賞》與《文藝風向》,春樹推出了自己主編的《繆斯超市》,饒雪漫又主編出版了《17》,盛大文學推出涅槃灰等領銜的《青瞳Ai小說》,磨鐵圖書推出南派三叔主編的《超好看》等等。其中,《17》是以17歲少女讀者為服務對象;《青瞳Ai小說》主要側重于青春愛戀與都市言情,《超好看》則主要限定在玄幻、仙俠題材。
這種由青春作家主編雜志書的現象,是想用個人作為文學名人或偶像的影響力,對作家個人的名牌進行延伸,打造雜志書的名牌,壯大讀者群和發行量,滾動名聲和商業利潤。
作家和主編畢竟不是一回事,有的人可以兩者兼得,但更多的作家在寫好作品的同時,卻不一定能辦好一本文學雜志,所以,青春文學雜志書“群起而上”的結果是,有的雜志書必將因為虧損而被淘汰,少數則歷經市場考驗,在圖書和期刊市場上始終亭亭玉立。
(編輯:偉偉)
| · | 當代文學地理學與本土經驗 |
| · | 傲慢與偏見:文學的雅俗之變 |
| · | 這一代文學的表述 |
| · | 在文學的路上重新出發——“魯十九”學員代表畢業發言 |
| · | 文學變了,還是讀者變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