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人書事]越界?越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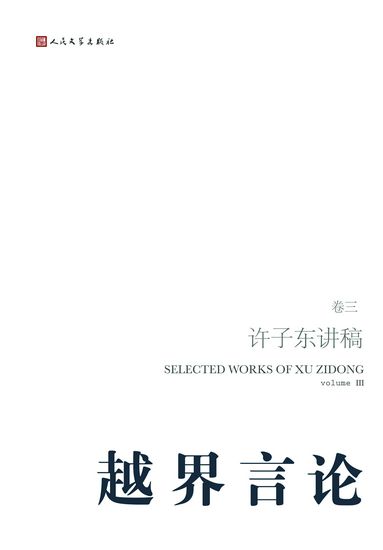
《許子?xùn)|講稿》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香港嶺南大學(xué)教授許子?xùn)|,與鳳凰衛(wèi)視《鏘鏘三人行》嘉賓許子?xùn)|,在學(xué)界與媒體間“越界”,在可言說(shuō)與“閃爍其詞”之間“越界”,在“可教育好的子女”、知青、煉鋼工人、學(xué)者、洋插隊(duì)、公共知識(shí)分子等多重身份之間“穿越”。近日,《許子?xùn)|講稿》(3卷本)由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這是許子?xùn)|著作在大陸首次結(jié)集出版。書中既有學(xué)院派知識(shí)分子許子?xùn)|關(guān)于“文革”集體記憶的獨(dú)特解讀,關(guān)于張愛玲、郁達(dá)夫、香港文學(xué)的深刻剖析,也有關(guān)于房產(chǎn)稅、潛規(guī)則的鮮辣酷評(píng),更有普通公民許子?xùn)|首度披露的苦樂人生,親歷講述、有料有味。是學(xué)院派,但不掉書袋;論文學(xué),也論世道人心。“越界人”許子?xùn)|攜新作走進(jìn)高校,第一站就是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與知名媒體人梁文道、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社長(zhǎng)潘凱雄暢談越界的可行性,上演越界版鏗鏘三人行。
沒人說(shuō)蘇東坡越界不對(duì)
就好像古時(shí)縣官去做木匠、大家子弟去唱戲一樣,當(dāng)下被批評(píng)很多的是學(xué)者出現(xiàn)在大眾媒體里面,被視為不務(wù)正業(yè)。梁文道對(duì)此持不同的意見。他介紹說(shuō),在最初找許子?xùn)|做《鏘鏘三人行》節(jié)目時(shí),許子?xùn)|也有一個(gè)心結(jié)放不開,就是作為學(xué)者跑到電視上拋頭露面不太像話。“我們認(rèn)定學(xué)者該是怎么樣,比如說(shuō),學(xué)者不該學(xué)粗話,學(xué)者不該做電視,學(xué)者不應(yīng)該如何。學(xué)者一做這個(gè)事情就是越界了。就像許子?xùn)|老師的第三本書《越界言論》,我想指出越界是必要的,甚至是非常好的一件事,為什么呢?我們首先看看,我們講越界的時(shí)候是越什么界,這個(gè)界怎么形成?界并不是從來(lái)如此的,它是歷史的產(chǎn)物,是不固定的。”
蘇東坡的身份是什么?梁文道拋出這樣一個(gè)問(wèn)題。蘇東坡是畫家,是詩(shī)人,是散文家,是美食家,是時(shí)尚達(dá)人,是官員,是異見分子。“哪一個(gè)是他的身份?在蘇軾的年代大家不會(huì)覺得這是一個(gè)困擾的問(wèn)題,因?yàn)楣賳T寫詩(shī)寫得好,好像不成為問(wèn)題。但是今天官員得了魯迅文學(xué)獎(jiǎng),我們會(huì)覺得是一個(gè)問(wèn)題。”所以,梁文道認(rèn)為界觀念是不斷變動(dòng)的,我們只是重復(fù)堅(jiān)持某種社會(huì)上固有的、臨時(shí)的關(guān)于界限的觀念,憑什么必須堅(jiān)持它而不能挑戰(zhàn)它呢?
界是怎樣形成的?梁文道指出,五四時(shí)期,大作家林語(yǔ)堂、胡適、魯迅等沒有誰(shuí)說(shuō)在報(bào)紙上寫文章就是越界了。魯迅在大學(xué)教書,同時(shí)也在《申報(bào)》開專欄“自由談”,拿稿費(fèi)。“所以曾經(jīng)有一個(gè)階段,不要說(shuō)蘇東坡的時(shí)候,現(xiàn)代文學(xué)階段的作家發(fā)表文章的陣地就是各種各樣的。我們現(xiàn)在很多人做研究會(huì)看到,魯迅文章旁邊就有花露水的廣告,就有一些商店一些圖畫。如果今天的學(xué)者恥于將作品跟那些東西放在一起,一定要在一個(gè)純粹的地方發(fā)表看法,我覺得未免太過(guò)了。”
越界是美好的
法國(guó)哲學(xué)家德勒茲曾這樣講過(guò)越界:社會(huì)不斷把我們的生活疆域化,我們則不斷地逃逸它,然后它依舊不斷地疆域化,在整個(gè)運(yùn)動(dòng)過(guò)程中,我們追求著逃逸的路線。梁文道表示,不斷逃跑,不斷動(dòng)搖舊界限并畫出新的界限,是非常重要也是美好的事情,要不然我們會(huì)被綁死在里面。
梁文道認(rèn)為,界限還在于我們思考社會(huì)或者人生或者世界的時(shí)候,腦子里面有很多框。“當(dāng)界被敲破或者被動(dòng)搖,你當(dāng)然會(huì)覺得人生好像很不穩(wěn)定,但是它其實(shí)會(huì)給你很大快感。”
一堆柜子,這個(gè)里頭放一些甘草,那個(gè)里面放一些牛黃,然后按方抓藥。中醫(yī)的這種方式讓梁文道感慨:“我們?nèi)绻J(rèn)為所有的社會(huì)問(wèn)題、公共生活都可以用這種撿中藥的方式分類安排范疇化來(lái)處理的話,那么我們就很危險(xiǎn)了,等于已經(jīng)認(rèn)為這個(gè)社會(huì)各種界限很穩(wěn)定了,各種問(wèn)題都已經(jīng)有專人給你解答了。”但是事實(shí)上,這個(gè)世界有很多嶄新的東西,有很多新的問(wèn)問(wèn)題的方式,新的解決老問(wèn)題的方式,都是由于對(duì)這些界不滿,重新穿越,甚至漠視它們的存在而產(chǎn)生的。
作為越界人,許子?xùn)|講了他自己的經(jīng)驗(yàn),就是在打算越界前,首先要做好本分,把兩件事分開,不依靠在外的言論追求學(xué)術(shù)上的地位;而當(dāng)你離開領(lǐng)域去發(fā)表言論的時(shí)候,就不是作為一個(gè)教授,甚至不是作為一個(gè)知識(shí)分子在發(fā)言,而只是盡公民的責(zé)任,是作為納稅人的權(quán)利,是作為老百姓來(lái)說(shuō)話。“我一越界就是公民。做好本分工作,然后做一個(gè)本分的公民。我認(rèn)為現(xiàn)在一個(gè)讀書人,作為一個(gè)公民,對(duì)于任何公共事務(wù)不發(fā)表意見的話,是不負(fù)責(zé)任的。”這種超越了個(gè)體身份的越界,這種對(duì)于更廣泛話題的言說(shuō),在許子?xùn)|看來(lái),其實(shí)也恰恰是自己作為社會(huì)一員的“本分”。
(編輯:偉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