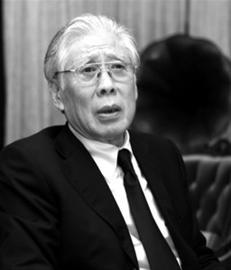
昨天下午,摘得第23屆上海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特殊貢獻獎的“話劇皇帝”焦晃在白玉蘭戲劇藝術論壇開講,細述從藝60年 “戲劇理想和戲劇人生”:“我的整個青春和生命,都給了舞臺。我個人生活挫折很多,舞臺是我唯一的天地,只要到了舞臺上,我就能把一切雜念都撇掉。 ”而此前,他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更是笑憶崢嶸歲月,從那些校園時光和生活點滴之中,也可以梳理出這位“話劇皇帝”到底是怎樣煉成的。
一次朗誦讓我踏上演藝路
少年時期的焦晃,因為戰亂隨父母在北京、重慶和上海之間多次遷轉。 8歲時在重慶偶然看到陳白塵的《禁止小便》以及老舍和宋之的合作的《國家至上》演出,與戲劇有了最初的接觸。
后來轉到上海讀初中,焦晃回憶:“我初二的時候,人家都是少先隊大隊長,都是團員,我還在那兒打彈子呢。有一次在課堂上,老師讓我念篇語文課文,我當時傻了,上海話我只會說,不會念,我一念,那就是北京話。但沒辦法,也只能硬著頭皮念。念完之后,整個教室里鴉雀無聲,我想完了,他們有得好笑話我了,哪想到所有的人都非常驚訝地望著我,想你這家伙還有這一手。我想著恐怕就是人的審美總是普遍的。 ”后來,看中焦晃的京腔京韻,老師把他推薦進了學校的戲劇組,“演戲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很莊重,一下子就從這打彈子的調皮搗蛋中出來了。 ”
到了高中,焦晃已經篤定自己要走演藝之路,他一邊廣泛閱讀文學名著,一邊用打壘球的方法鍛煉自己的形體、反應力和爆發力,立志要考上上海戲劇學院。父親一直希望他考理工科,但焦晃很清楚自己的思維模式,所以后來不顧父親的反對,堅持去考上戲:“當年有親戚問我,你既然要考,那你知道到底什么是戲劇?我那時候答不上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戲劇是人們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要感召人們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世界;戲劇也是一面鏡子,讓人更清醒地認識生活和自己,去掉盲目性,激發自覺性。 ”
“話劇演員的生命”在上海
“很多人以為我是北京演員,其實我出自上海戲劇學院。 ”焦晃一直強調,自己“話劇演員的生命”就是在上海。 1955年,焦晃如愿以償考上了上戲表演系,受教于前蘇聯專家葉·康·列普科普斯卡婭和朱端鈞、胡導等戲劇大家。連“客串”的教師陣容,都是當時的天王級人物——教臺詞的是京劇表演藝術家艾世菊:“那會兒他穿得樸素啊,被門房攔下來,他一氣之下,不來了。我們光知道他要來,等了整整一個多月,他怎么還不來! ”好在后來艾世菊還是來教授了焦晃和他的同學們自己最擅長的“白口”:“艾世菊老師,他總是知道戲扣兒在哪里。 ”而教芭蕾舞的則是中國第一只“小天鵝”胡蓉蓉:“第一次上課,她一開始覺得我不行,沒想到我一彎腰,比那些女將還厲害,她說‘哎!你行!你行! ’后來還差點把我弄去跳芭蕾。 ”
回憶起來自列寧格勒戲劇表演學院的蘇聯老太太葉·康·列普科普斯卡婭,焦晃說:“我至今還記得,第一天上課時,她就送了我們一堆巨大的積木,讓大家展開想象做游戲。她說,演戲不為觀眾而存在,演戲就像小孩玩積木做游戲——他們在辦家家的時候,是最最真誠的。 ”
在上戲時,焦晃這幫學生被要求“睜開眼睛,人就要在戲中”。在演繹《祥林嫂》時,他們從賀老六搶親開始,扮演祥林嫂的女生還在學校里散步,他們把她扛起來就走,“祥林嫂”一邊掙扎,一邊吐他們唾沫,他們沒辦法,還找了塊擦黑板的抹布,塞到了她嘴里,而當“劇情”進行到“阿毛之死”的時候,焦晃演的,就是那只叼走阿毛的狼:“我跑得快啊,滿世界逃,他們發動了全校學生,說那只狼把阿毛叼走了,滿世界抓我都沒抓到,氣得要命,連連說:‘這只狼惡苛的! ’”
如果不演戲快樂也就沒了
上戲的學習生涯確定了焦晃的藝術審美準則:“我一生都沒有悖離過斯坦尼體系,沒有悖離過‘行動規律’(表演學說)。 ”
焦晃早年主演的莎士比亞劇作《無事生非》和《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曾轟動一時,使他贏得了“莎劇王子”的美譽;他在莫里哀的劇作《吝嗇鬼》、美國當代劇作《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一個黑人中士之死》以及英國品特的劇作《背叛》中的出色表現,令幾代話劇觀眾贊嘆。可以說,由焦晃主演的近百部戲劇和影視作品,已足以構成一道色彩斑斕的戲劇舞臺人物長廊,他的精湛技藝,他的敬業精神和他那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為中國戲劇藝術作出了特殊貢獻。
對于舞臺,焦晃依然充滿偏愛也充滿期望,“劇場是我心里最神圣的地方,當時我們在長江劇院演出,我總是最后一刻才離開劇場,那些票務和清場人員,都陪到我最后。之前我們這批曾經在長江劇院待過的人聚會,一看到大家,我的眼淚就再也止不住了。 ”提起近兩年參與創作的《欽差大臣》和 《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他很樸素地表示:“沒什么為什么,我就是想演個戲,想在有生之年再多演些戲,如果不演戲,快樂也就沒有了。 ”他更風趣地打比方道,“我就像個拿著掃帚掃大街的人,如今退下來了,可是掃帚還在我手里啊,我就算掃不了大街了,我掃掃家門口吧,我不掃難受啊! ”
回憶自己的舞臺生涯,焦晃說:“我這輩子做得微不足道,但是盡了我的心,盡了我的力,很誠實地付出了勞動,我沒有愧對,心里還是很踏實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