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總是離土地最近的人——編劇蘆葦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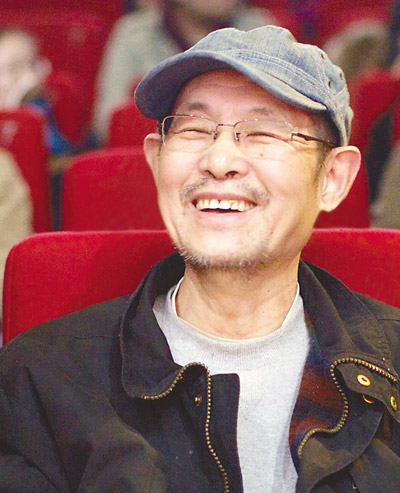
蘆葦在新書發布會上
“過兩天我將去歐洲度假,打算帶兩部中國電影的碟片過去,向那邊的朋友介紹一下中國文化。我的一位朋友是生活在丹麥的美國人,他僅看過兩部中國電影,便問我帶什么電影過去,我說是《霸王別姬》和《活著》,他說,太巧了,我看過這兩部電影。”日前,在蘆葦電影回顧生涯暨《電影編劇的秘密》新書發布會上,一位女觀眾現場說道,而這兩部電影的編劇正是蘆葦。
蘆葦,何許人也?他是《霸王別姬》《活著》的編劇,這兩部電影給陳凱歌、張藝謀、葛優帶來了國際性的聲譽,他還是《圖雅的婚事》的編劇,這部電影讓第六代導演王全安斬獲了當年的柏林電影節最高獎——金熊獎。近年蘆葦得以投拍的作品少了,但他依舊筆耕不輟,比如他根據中國現代舞第一人容齡公主與光緒皇帝的傳奇故事創作了史詩氣象的《龍的親吻》;他還根據一位普通農民的日記改編創作了劇本《歲月如織》;蘆葦亦曾應香港導演陳可辛之邀,改編美籍華人作家哈金的同名小說《等待》。令人惋惜的是,蘆葦五年七易其稿的劇本《白鹿原》,最后被拍得面目全非;未被香港導演吳宇森采用的《赤壁》,這次附錄在《電影編劇的秘密》一書后面,使得觀眾能夠通過電影劇本的格律去看這段歷史。蘆葦列了兩萬字提綱的《杜月笙》,這個承前啟后的人物已經躍然成型。此外,蘆葦還為日本導演小泉堯史撰寫了《李陵傳》,為法國導演讓-雅克·阿諾改編了《狼圖騰》,而后者正在熱拍。
“哥早已不在江湖,但江湖上一直流傳著哥的傳說。”早年記者在西安求學時,曾與蘆葦在一家音像店淘碟,但未得際會因緣。那時音像店店長對記者說:“每當葦哥(蘆葦)有外國朋友來時,他便來我們店拿一些《活著》的碟片送給他們,為了他,《活著》是我們店的常備項目。”因此,記者知道了《活著》是蘆葦比較滿意的作品,音像店店長活潑的表述,讓記者以為蘆葦是一個長發飄飄、很有喜感的人。直到在新書發布會上第一次見面,眼前出現的竟然是在西安大街上最常見的一個普通老漢,誰能想到這人就是赫赫有名的編劇蘆葦。記者不禁想起了宮白羽筆下的太極高手陳長興,也是遁隱農村的一個農民,高手總是離土地最近的。對蘆葦的印象瞬間與其作品給記者的感受應和起來,應該是他,也只能是他,才能寫出那些帶有清香泥土、綿密生活、厚重歷史、地道類型的作品。
蘆葦這樣表述他與土地的關系,“當年插隊的時候下場大雪,內心特別激動。因為我知道可以吃飽了,這場雪一下,麥子的收成就有指望了。瑞雪兆豐年,這事重大而幸福”。鑒于此,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電影《白鹿原》的癥結所在,“我當過農民,是在《白鹿原》的環境下生存過的人,我跟那塊土地和那些人的情感息息相通……拿著這么好的題材,拍出一部不受觀眾待見的電影來,只能證明電影人的無能無知”。
良藥苦口,但現在敢于開良藥且能開良藥的一線電影工作者鳳毛麟角。曾因為《南京!南京!》被蘆葦批為“頭腳倒置、妄扣主題”的陸川說:“在拍電影之前,我們都敢說真話,當我們拍了電影之后,便很少說話了,但蘆葦老師還敢說實話,我就想,難道蘆葦老師不想在圈里混了嗎?”蘆葦的言論不避親疏,率性直言,他評價“第六代”導演道:“第六代的人文傳統非常薄弱,作為藝術家他們的胸懷和眼光都比較狹窄……而電影應該是小人物、大格局。要折射大時代、大精神、大情感。人物可以小,精神不能小。”同樣,他還對合作過的陳凱歌等“第五代”導演點名批評,“狀態好的時候,人可能有神的光環;狀態不好的時候,也就是一俗身而已。你能相信拍《霸王別姬》的導演后來也拍出了《無極》嗎?”對于近年頂著藝術片導演光環的顧長衛,蘆葦“蛇打七寸”:“《孔雀》和《立春》拍的是底層人,可是真的不了解底層人,人物扭曲失形、難以靠實。視角高人一等,在潛意識里有病態的優越感,這兩部電影的人物都有一種病態的卑賤感。”蘆葦調侃自己“比較閉塞”,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則說:“蘆葦就像一只特立獨行的豬。”不管是閉塞,還是特立獨行,這都說明了蘆葦在電影界里超然的位置,超然才能獨立,敢說真話。
影迷心中總有一種情結,在他們中間流傳著美國導演昆汀·塔倫蒂諾在錄像帶租賃店當店員的“藝術人生”,法國導演特呂弗偷電影海報的故事,也有蘆葦怎樣從美工自學成才,成為編劇的段子。這些故事和段子鼓勵了很多非科班的電影發燒友,扛起了攝像機,甚至拿起手機去拍電影。在發布會現場,當觀眾問蘆葦怎樣才能成為編劇時,蘆葦回了三個字“去寫吧”。但蘆葦寫劇本也并非全憑一腔熱情,在他看來,寫劇本首先是一門手藝。在做編劇之前他是電影發燒友、音樂發燒友,每次看好電影都要做大量筆記。除此之外,他還認真讀過美國人悉德·菲爾德的《電影劇本寫作基礎》和路易斯·賈內梯的《認識電影》,越是有縱深感、有情懷的影片,越需要扎實的寫作技巧來支撐,《霸王別姬》這樣一個不易入手的京劇題材影片能一下子抓住了觀眾,并且一唱三嘆、蕩氣回腸,與蘆葦對類型片的精細揣摩是分不開的。蘆葦說:“類型實際上是一個交流系統。當你把類型規定好以后,觀眾就有所期待。比如冰箱是家電的一個類型,觀眾一聽說就知道可以放食物進去。”
除了電影方面的書籍,蘆葦還特別提到了《外國文藝》,“它對于中國一代人的文化啟蒙成長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包括蘇童、莫言這代人。莫言的《紅高粱》是從《外國文藝》里面學的,一個美國華裔作家,叫湯婷婷(英文名:Hong Kingston),她曾寫過一本書叫《內華達山脈的爺爺》,曾發表在這本雜志上。兩者一比,你就知道《紅高粱》是模仿它,而且模仿得很開竅,它是有出處的”。
“曹操沉迷魔境意猶未盡地說:亦即詩意的境界,天籟地聲的境界,就像這個狗日的孫叔材!”這是蘆葦的《赤壁》中的臺詞,曹操沉迷魔境的狀態,讓人不難想起《霸王別姬》里程蝶衣的“不瘋魔,不成活”的藝境。這也是蘆葦的工作狀態。紀錄片導演徐童說:“今年夏秋之間,我和蘆葦老師在藏族聚居區采風,其間遇到了很多艱險,像高原缺氧,蘆葦老師畢竟是60多歲的人了。當車陷到泥沼里面時,蘆葦老師也是第一個沖下去搭墊板,推車。蘆葦老師看到他感興趣的素材和人物時,總會積極地拍攝、傾聽。回來之后,蘆葦老師就住院了。當時我在想是什么樣的動力讓一位編劇冒著生命危險去采集生活,像蘆葦老師這樣技巧卓越、經驗豐富的編劇,我一直以為他坐在電腦桌前就可以寫作了,其實是因為他內心裝著價值觀的標尺,就像他自己說的,‘我覺得展現人道精神和人性是電影的終極價值’。”
蘆葦作品中的人道精神和人性是什么呢?在《電影編劇的秘密》中,談及蘇聯導演塔爾可夫斯基和其電影《安德烈·盧布廖夫》那一節,蘆葦說,塔爾可夫斯基的鏡頭對準的是俄羅斯民族的靈魂質感,這永遠是他的主題。蘆葦對自己的要求則是:“一直力攻正劇和悲劇電影,希望能在這兩個類型上取得進展,能夠跟別的民族平等對話,取得彼此的尊敬”。(記者 張成)
(編輯:子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