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何處覓大師?——卞毓方與他的《尋找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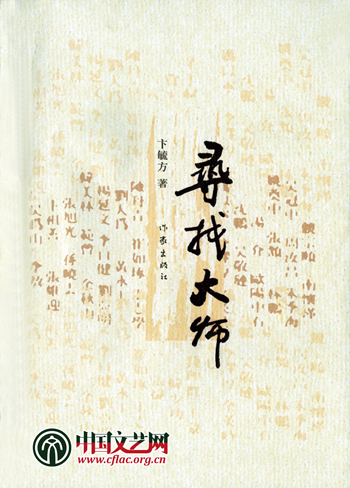
《尋找大師》 卞毓方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大師是一道風景。尋找大師的卞毓方把自己變成了一道風景。
譬如說訪問饒宗頤先生,他老人家住在香港,九十多歲,和卞毓方隔著山,隔著海,隔著年齡的鴻溝、學問的峰巒。“想見上一面,很難的啊!”卞毓方說。
但是既然打定主意要見,卞毓方就開始扎實地做事。首先買了饒宗頤的書讀,幾乎能買到的,都買了,揀看得懂的翻,看不懂的,暫時放在一旁,文如其人,讀了著述,等于見到了半個人。這樣一來,卞毓方就更加想一睹饒先生的風采。
有一天,卞毓方永遠不會忘記,2010年7月11日,雕塑家紀峰告訴卞毓方一個信息:8月7號,饒宗頤將去敦煌過生日。而且,他跟饒先生周圍的人熟識。簡直是天賜良機,無論如何不能錯過。卞毓方當機立斷,買了8月6號的機票,飛赴敦煌。從意外里鉆出驚喜,卞毓方得知,饒先生乘的也是同一趟航班,只是在頭等艙,不便見面。此時此刻,卞毓方才確信老人家到敦煌不是傳說,之前他心里還并不確定,一直忐忐忑忑。第二天傍晚,在給饒先生祝壽現場,卞毓方如愿以償見到老人家。所謂如愿以償,包括握手、照相、講話。人潮洶涌,眾星捧月,他只來得及向老壽星說上一句:
“我是季羨林的學生,從北京來看您。”
饒先生握了握他的手,吐出一個詞:“哦——”
事后,在京城某高校,卞毓方向愛好文學的學生回憶起這段故事。有人問他:“您就說了一句?”“就一句。”“饒先生就答了一聲‘哦——’”“就一聲。”“您怎么去的?”“我說了,坐飛機啊。”“不,我是問您飛機票能報銷嗎?”“我是自動跑去的。饒先生沒有請我,也沒有誰派我,那機票我還存留著,你是想給我報銷嗎?”引來滿堂大笑。
就一個“哦”,這見面與不見面,又有什么區別呢?但卞毓方卻說:“見之前,饒先生離我很遠很遠,仿佛在另一個世界;見之后,饒先生就變得近在咫尺,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一念心馳,于抬頭、轉身之際,準能感受到他灼熱的呼吸,看到他矜持的微笑。”
是不是有點玄乎?但是,報告文學作家黃傳會對這一點卻深有同感。為了寫羅陽的傳記,黃傳會希望見一下羅陽的愛人,卻被拒絕,她任何記者都不見。“我要給羅陽寫傳,他愛人都不見,這個事情就很別扭。”經過千方百計努力,羅陽的愛人最后見了黃傳會一小時。時間不長,但對黃傳會來說已經足夠,羅陽在他心目中就活起來了。“有的人說不見拉倒,但是見跟不見完全不一樣。我知道羅陽跟這個人生活了二十幾年,別人給我講的那些故事就活起來了。這種作家的苦心,很多人是難以理解的。”
卞毓方的職業是記者,慣于寫人。1995年正式動筆寫散文,以人物為主,且都是馬克思、愛因斯坦、毛澤東、陳獨秀、馬寅初、胡耀邦、錢鍾書,以及蔡倫、文天祥、哥倫布等等大人物。這么多年寫下來,在文學界已頗有影響。按說成名成家的人,往往都不會再放下身架去追星,但卞毓方偏偏放下了。
尋找大師的過程中,卞毓方選出了一些人物,他們是饒宗頤、南懷瑾、吳冠中、周汝昌、朱季海、姚奠中、張頷、林鵬、湯一介、歐陽中石、沈鵬、吳敬璉、厲以寧、余英時、木心、王蒙、賈平凹、韓少功、莫言、張煒、陳丹青、崔如琢、于志學、劉大為、黃永玉、楊延文、李自健、劉亞明、韓美林、范曾、余秋雨、張旭光、孫曉云、卞祖善、吳為山。這些人大多學有專長,影響不小。
既然名為“尋找”,就并非斷語,書中之人是不是大師,依然有很大爭議,還需留待歷史驗證。不過一路采訪過來,當被問及最大的感慨是什么時,卞毓方卻說:“堂堂中華,難覓大氣象者。”背后原因,卞毓方說,成大師者,思維要求突破,要求不拘一格,這就產生了矛盾。另外還有金錢的壓力。本來他以為,錢多了有利于產生大師,實際情況卻是,錢把中國人壓垮了,形而下的意志讓形而上俯首稱臣,官員垮于錢,知識分子也垮于錢。
卞毓方說,尋找,是一種過程。找的本身,往往比結論更有意義。一切都是相對而言,在一個沒有屈原的春秋戰國,他會把桂冠贈給宋玉。不對大師絕望,拔腳出發,就是因為他對文化崛起仍滿懷期待。
(編輯:曉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