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夢的出版人”
一個“有夢的出版人”(中國出版掌門人)
——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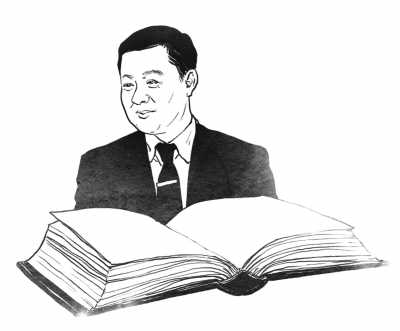
徐經緯繪
有人說他是富有遠見的戰略家,有人說他是勇立潮頭的革新派,有人說他是游刃有余的社會活動家,有人說他是不知疲倦的工作狂,有人說他是感染力極強的演講家,有人說他是精明老辣的生意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卻稱自己只是一個“有夢的出版人”。
“25年前,我們帶著理想來經營這家出版社;未來的25年,我們有更大的夢。我們尊重學者、敬畏學術,力爭做國內最好的學術出版社,搭建全方位的高端學術出版平臺,推動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5周年社慶時,謝壽光如此描繪心中的“中國學術出版夢”。
謝壽光是一個富有戰略眼光的人,正是這種素養造就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后來居上。1997年9月,謝壽光從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調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擔任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翌年出任社長兼總編輯。彼時,只有13年歷史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沒有豐厚的家底,全社僅有23名員工,年出書不到100種。“這樣一家無名小社,想做大做強,很難!”在謝壽光特意舉行的支招獻計會上,蘇國勛、李培林、沈原等學界同仁長嘆。
當時,在市場經濟大潮沖擊下,不少學術出版社都選擇“往下沉”,著力于大眾出版,謝壽光卻堅持“往上走”,將出版重心定位于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圖書。“在出版領域,我們不可能包打天下,教材、教輔、少兒等圖書產品必須舍棄。”謝壽光分析道,“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直屬出版機構,我們應該在最有可能形成品牌、影響力和競爭力的領域占據我們應有的位置。”
如今,憑借16年的堅守與積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創社科經典,出傳世文獻”的出版理念和“權威、前沿、原創”的圖書定位贏得學界廣泛認可。在謝壽光的帶領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保持年均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北三環全資購得7000多平方米的辦公用房,員工近300人,年出書1300余種。社會學、近代史、蘇聯東歐研究等專業圖書在出版界獨領風騷,經濟管理、國際問題、古籍文獻等主題圖書亦別具特色,學術期刊、電子音像、數字出版、國際出版齊頭并進。謝壽光自己也先后榮獲“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第十屆韜奮出版獎”、“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崗位先進個人”等獎項,成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之無愧的掌門人。
謝壽光開創了一種名為“皮書”的全新出版形態和圖書品牌,迄今已累計出版1300余種。經過近20年的精心打造,皮書作為一種智庫產品,不僅成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出版品牌,而且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乃至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術品牌,還被納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系和“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
謝壽光早在十多年前,就感覺到信息技術可能給傳統出版帶來沖擊,在他的帶領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早在十多年前就邁開信息化與數字化的步伐。在信息化的浪潮中,謝壽光趨新而不躁進,主張“我們是圖書出版者,更是人文社會科學內容資源經營商”,堅持“以我為主”和“小步快跑,分段推進,適時整合、升級”的原則,建成了具有中國專業出版社特色的數字出版經營模式。
做王云五那樣的出版人,辦令人尊敬的出版機構,是謝壽光不懈奮斗的目標。“學術出版是最講究傳承的事業。只有幾代人的厚積,才會有某個階段的薄發。相比于百年老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歷史還太短。”展望未來,有著強烈危機意識的謝壽光不無憂慮卻信心滿懷,“我們會繼續堅守學術出版方向,用出版來促進學術研究的規范與深化,實現知識的積累,從而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學術話語權和影響力。”
基于此,謝壽光代表50多家出版社在原新聞出版總署召開的座談會上呼吁進一步提高學術著作出版門檻,并承擔起學術著作出版規范國家標準的起草工作。同時,他還精心組織學術演講、訪問交流等高規格的學術交流活動,擴大中國專家學者及其學術成果的國際影響力,致力于中國學術“走出去”。
社長之外,謝壽光還擔任中國社會學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調查與研究中心副主任,并兼任多所大學與研究機構的教授,在教書、演講、科研、出版諸角色間轉換自如,被譽為精力充沛的多面手,他卻謙稱至多只是一位“雜家”。自稱“學術票友”的他,在多個研究領域都有所建樹,并深度參與了中國社會學會的恢復與重建工作,彌合了當時學界內部的分裂與沖突。知名社會學家陸學藝曾贊譽說,他們那一群人都是謝壽光這樣的編輯給培養出來的。
雖然成就卓著,謝壽光卻稱這不過是“時勢造英雄”。這位1977級的廈門大學高材生,有著他那一代人的審慎與穩練。媒體朋友們更多是從社科文獻出版社有著濃厚學術底蘊與現實擔當的產品中,窺見他作為出版人的理想與抱負。
時至今日,兩鬢斑白的謝壽光依然率領一群年輕人奮斗在一線,推進信息化與數字化,釋放員工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加強五大出版能力建設,創建研究型的出版機構,打造標準普爾那樣的指數庫……很多人不解:16年了,社長還沒當夠?何必把自己弄得這么累?他卻回應道:“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想,我還有好些年和大家一起奮斗的時光,爭取再創20世紀三四十年代商務、中華那樣的輝煌。”
(編輯:竹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