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香椿樹街”要寫一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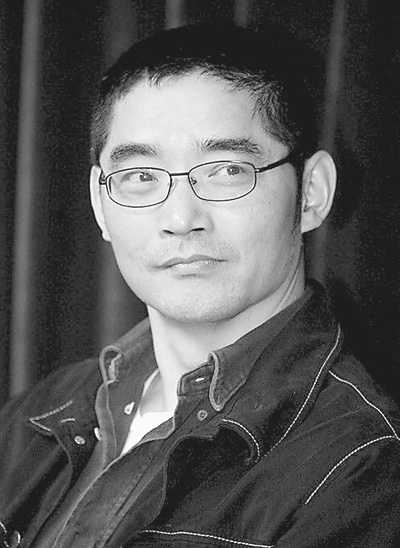
香椿樹街,一群在街上晃晃悠悠的少年……那時(shí)候的天空湛藍(lán)、陽光燦爛,但是沒有陽光的日子更多,陰郁的、悠長而寂寥的小巷,承載著蘇童少年的惆悵。他以童年的視角穿越時(shí)空,那時(shí)的他愛沿著香椿樹街奔跑,不見得多快,但是奔跑的姿勢(shì)獨(dú)特,足以讓人記住,那個(gè)奔跑的孩子就是蘇童。
他總想跟別人不一樣,就像一個(gè)調(diào)皮的孩子,闖入秩序井然的屋子,那里有眾多競相“講故事”的能手。他用尖叫引起別人的注意,然后很瀟灑地吹著口哨離開,似乎目的僅在于此。
在蘇童的創(chuàng)作中,童年是個(gè)獨(dú)特視角。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透過童年的望遠(yuǎn)鏡照見現(xiàn)實(shí)的生活,有時(shí)是某些記憶的碎片,有時(shí)是垃圾或者香煙殼。一個(gè)從未出過蘇州城的孩子,對(duì)這些格外敏感,這讓他能最大程度地利用童年的記憶,呈現(xiàn)所謂狹窄封閉又充滿野性的孩子的生活狀態(tài)。
“我一直在挽留這個(gè)敏感,通過小說的方式。挽留的渠道差不多,但有時(shí)會(huì)在剎那間突然想到幾十年來從沒有想過的一個(gè)人或一件事,我特別珍惜這樣的時(shí)刻,對(duì)我來說,小說來了。”童年記憶保留到現(xiàn)在,定是有價(jià)值的東西,對(duì)蘇童而言,直覺很重要。
20世紀(jì)80年代,他陸續(xù)完成的“紅粉系列”,均以女性為主要描寫對(duì)象,比如《妻妾成群》、《紅粉》、《一種婦女生活》和《另一種婦女生活》。因?yàn)椤镀捩扇骸繁粡埶囍\改編為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蘇童被貼了“女性寫作”的標(biāo)簽。他的另一個(gè)標(biāo)簽,是歷史題材的創(chuàng)作。《碧奴》和《武則天》的寫作,是幻想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實(shí)現(xiàn)。蘇童說,他個(gè)人看重寫作中的這個(gè)環(huán)節(jié)。他希望是一個(gè)非常完美地利用幻想現(xiàn)實(shí)主義寫作的作家,“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的態(tài)度,作家不應(yīng)陷入現(xiàn)實(shí)的泥潭,不能自拔,必須學(xué)會(huì)進(jìn)退有余,離地三公尺飛行。”
他身上沒間斷過“標(biāo)簽”:尋根文學(xué)、先鋒文學(xué)……其實(shí)在他心里,作家哪里需要站隊(duì)?不僅不站隊(duì),還要徹底打亂。無折騰就無小說。于是,孩子氣的“尖叫”之后,隨著年歲漸長,蘇童換了一種“折騰”方式。“對(duì)別人來說是回歸,參照我自己的經(jīng)歷來說恰好是創(chuàng)造。在那之前我沒有按照傳統(tǒng)的路數(shù)寫過小說,沒有認(rèn)真塑造過一個(gè)人物。《妻妾成群》之后,我又變成一個(gè)新來者。”蘇童說,所謂前進(jìn)的方式其實(shí)是后退,《妻妾成群》是他后退一步的結(jié)果,他的表達(dá)方式有了明顯變化。
調(diào)皮的孩子在故事中找到了樂趣,并沉浸其中樂不思蜀。他在一部部小說里培育生命,和他們朝夕相處然后分手,如一場場艷遇,但是跟欲望無關(guān);他在故事的河流里潛入又浮出,四處游蕩。《1934年的逃亡》、《少年血》以及《河岸》,“逃亡”在他的小說里都是一貫穩(wěn)定的因素;“河流”也是須臾不可缺少的背景。在新作《黃雀記》里,蘇童的這些特點(diǎn)依然存在。
“放逐是我比較迷戀的小說主題。有好多小說會(huì)不由自主地契合這個(gè)主題。逃亡是一種顛覆,顛覆他人所說的小說秩序。”蘇童說,很多作家都有意做一個(gè)對(duì)故事常規(guī)或形式上的破壞者。他的“破壞”更有挑戰(zhàn)性,是因?yàn)樗辉卩]票大的地方做道場。他說,“香椿樹街”要寫一輩子,不會(huì)厭煩。
這次他“畫”的郵票叫《黃雀記》,仍然是香椿樹街的故事,但整個(gè)故事歷史時(shí)間拉得比較長。他力圖使自己的作品面目復(fù)雜,而不是做一個(gè)簡單地被一兩句話概括的作家。“倒不是有意樹立復(fù)雜多變的形象,我的創(chuàng)作一直想自我調(diào)整,設(shè)計(jì)一個(gè)模糊的未來,設(shè)計(jì)所謂如何說故事。過去的講述還沒有剖析到人物的靈魂深處;《黃雀記》不同,我很努力地寫到最深處,像一道光,像一把刀,切入最深的地方,不能再往前走一寸為止。”蘇童說,書里的人物形象塑造之鮮明,是他寫作以來最滿意的,以至于能夠“看見”他們。“過去我也在努力塑造人物,但沒能‘看見’他們;《黃雀記》的寫作,是人物離我最近的一次,每一個(gè)章節(jié)寫作中的相處,我都能感覺到他們的呼吸。寫到某個(gè)對(duì)話時(shí),如果寫得不妥當(dāng),人物會(huì)自動(dòng)糾正我:應(yīng)該這么說話。”
《黃雀記》的結(jié)尾,失魂的爺爺懷抱帶有胎記的嬰兒。那胎記是羞恥的記憶還是其他?那懷抱的是溫暖還是桎梏?蘇童不說,只是神秘地微笑,把更大的懸念留給你我。
(編輯:偉偉)
| · | 90后接過蘇童手里的獎(jiǎng) |
| · | 《收獲》刊發(fā)《黃雀記》 蘇童自刪5萬字 |
| · | 短篇小說的境遇與出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