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后的詛咒與祈禱——讀曹明霞長篇小說《日落呼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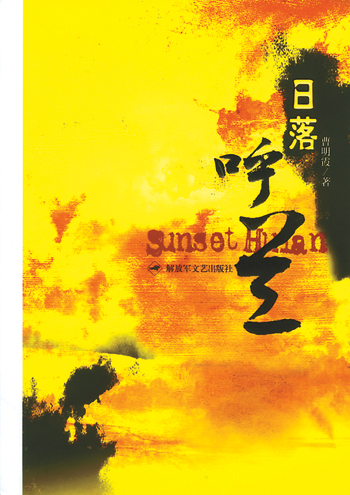
《日落呼蘭》
曹明霞 著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
從小說敘述的時間來說,曹明霞的《日落呼蘭》可以說是蕭紅《呼蘭河傳》的續篇。蕭紅筆下20世紀20年代呼蘭河畔民間的貧苦、愚昧、迷信、麻木一如既往,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又雪上加霜,苦難變成了災難,悲涼變成了悲哀。在《日落呼蘭》中,不要說普通的受難群眾,僅僅死難者就是一個長長的名單。
剛強的,柔弱的,勇敢的,膽小的,迷惑的,幼稚的,自私的,貪婪的,霸道的,殘忍的,良心未泯的,偽善真惡的,都在戰爭的浩劫中受難受死,誰也不能違背戰爭的邏輯。必須寫到各色人等的橫死、暴死、慘死、冤死、無辜的死、活該的死,否則就無法揭示戰爭的非人性、非理性,就無法有力地暴露戰爭的罪惡與荒謬。譴責戰爭,詛咒戰爭,是小說的主題,然而又不能把《日落呼蘭》籠統地說成是反戰小說。小說對日本侵略者搶劫殺人的暴行,對歸屯并戶、實行街村制的殖民統治,對開礦山、伐林木、修鐵路、建機場的經濟掠奪,對許多中國勞工喪身礦井、在火鋸廠里斷指盈筐的罪行都有充分的揭露,并多次借鐵驪鎮百姓的口指出,客人來到主人家,又搶又奪,又捉又殺,上逆天理,下悖人情,是不能接受的,從而沒有陷入不講歷史是非的泛人道主義的偏頗。《日落呼蘭》不是一般的反戰小說,而是一部在回顧與審視日本軍國主義者由囂張到潰敗、由炙盛到衰落的歷史之后,擺下亡靈為祭品,發大心愿,遙祭無數個無罪有罪的亡靈,發愿人類世界應該永久和平的祈禱之書。作品盯住的不僅是那些在戰爭中毀滅的人,更是那個制造人的毀滅的戰爭。長篇小說不怕說小故事,怕的是沒有大情懷,《日落呼蘭》就是一部從小鎮說起,在大格局大視野中體現大情懷的大書。
背靠1931年到1945年東北抗戰這樣的大背景,面對小鎮、平原、山林、雪原這樣的大場面,涉及百姓、抗聯、日軍、開拓團這樣紛繁的故事,把人物活動納入到15萬字的小說中,需要何等的腕力!作家沒有擺出一副指天畫地的架勢,只是用一支纖筆樸實平靜、工筆細描地講述著這片苦難土地上的日常生活,像一個早已流干了淚水的老人,回憶那些已經遠逝卻仍然活在她心中的往事,細節飽滿,具體而微,清晰真切,舉重若輕,整個小說像一篇故事版的21世紀的《吊古戰場文》,像一幅小說版的油畫《希阿島的屠殺》。細節飽滿往往篇幅就不容易控制,《日落呼蘭》剪裁果斷,基本上不做情節過程敘述,使作品情節跳躍而不失連貫,敘述從容而不拖沓,語言精煉而不干澀,顯出作家寫作經驗豐富,在結構和語言上用足了功夫。
小說在藝術上的成功,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作品的第一主人公不是抗日英雄,也不是在斗爭中成長起來的戰士。從14歲到28歲的洪慶山勤苦能干,善良仗義,又膽小怕事,是一個中國人和日本人人見人愛的好青年。他是家庭勞力的頂梁柱,也為日本人干活掙錢。他拒絕加入憲兵隊當特務,也不肯進山加入“山林隊”,他只是希望中國人和日本人“都老老實實過日子,誰也不招誰,誰也不殺誰的人”。最后在患難中與日本女人花田生下一兒一女,花田死后,又命中注定地要與日本姑娘純子一起度過剩下的日子。你可以不贊同他的和平幻想,卻深深理解和贊同他的和平愿望。在他卑微的身軀里,有一顆與全人類相通的高尚的靈魂。選擇這樣一個非英雄少血性的中庸人物在抗戰作品中做主人公,還是第一次出現。
第二是全書14章,從第5章起,日本來了開拓團。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就有小規模東北移民。1932年后,向中國東北移民成為日本國策,其目的是逐步改變滿洲的民族構成,永久占領東北,同時作為準軍事組織,儲備后備兵員。大規模的經濟“開發”使東北人民破家失地,成為日本人的廉價勞動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東三省秩序一片混亂,饑餓、寒冷、怕報復,“日本男人瘋狂地采用多襄井的辦法,殺死老婆孩子,再自殺,有縱火的,有爆炸的,一家一家的死,一片一片的燒毀房屋”,還有許多開拓團移民后來成為日本政府的“棄民”,反而是中國群眾收養了許多日本棄兒。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出現在小說里,具體地展現出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侵華戰爭,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反對和遏制罪惡的戰爭,應該是全人類的事業。相比起來,個別作品讓侵華日本兵在臨死的時候,從口袋里掏出妻女的照片,以顯示日本兵也有人性,就顯得幼稚淺薄了。
《日落呼蘭》發表在日本政府策劃“購買”釣魚島鬧劇引發中國東海局勢緊張之際,不知道作家的祈愿能否得到國際政治家們的重視?
(編輯:偉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