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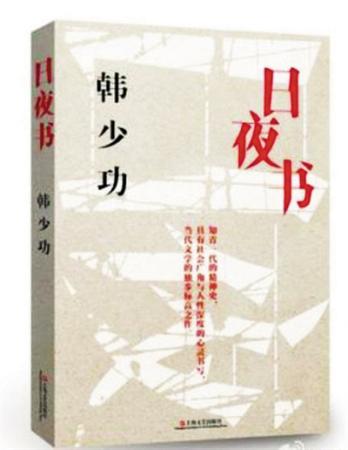
作家韓少功近日推出新作長(zhǎng)篇小說(shuō)《日夜書(shū)》,這是他繼《馬橋詞典》、《暗示》后的又一長(zhǎng)篇力作。這本描寫(xiě)知青群像的小說(shuō),描繪知青一代的心靈史和精神史,重點(diǎn)關(guān)注他們?cè)诋?dāng)下的命運(yùn)。
從《爸爸爸》到《日夜書(shū)》,韓少功的創(chuàng)作速度并不快,但每部作品問(wèn)世總能引發(fā)人們熱議。而另一方面,他也曾身兼數(shù)職,參與行政工作。2000年,韓少功辭去《天涯》社長(zhǎng)及海南省作協(xié)主席等職務(wù),每年有半年時(shí)間住在湖南鄉(xiāng)下。2011年,他未到退休年齡堅(jiān)持“裸退”,又放棄了海南省文聯(lián)主席和黨組書(shū)記的職位。
韓少功說(shuō)話溫文和藹,但言簡(jiǎn)意賅。電話一打就接,但是對(duì)于他自己覺(jué)得過(guò)于重復(fù)、自我宣傳的題目,一個(gè)都不答。他如今已年至花甲,笑說(shuō)自己正在“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
壹
“老馬”在中國(guó)的影響似乎被說(shuō)過(guò)了頭
羊城晚報(bào):從《爸爸爸》到《馬橋詞典》到《日夜書(shū)》,您的小說(shuō)敘事方式一直在改變,在文體創(chuàng)新上,您是否有預(yù)想的一個(gè)寫(xiě)作脈絡(luò)?
韓少功:沒(méi)有,完全沒(méi)有。寫(xiě)作受制于各種條件,而這些條件是不斷變化的,比如我只有面粉的時(shí)候就吃餅,只有大米的時(shí)候就喝粥,如果餅和粥都吃膩了,條件許可的話,我就試一下做法國(guó)大菜。哪一種小說(shuō)樣式最合適我,不是一個(gè)理論問(wèn)題,是一個(gè)實(shí)踐才能解決的問(wèn)題,得慢慢地試,得相機(jī)行事。
羊城晚報(bào):這么多年過(guò)去,現(xiàn)在回頭看《爸爸爸》,您是否會(huì)認(rèn)為當(dāng)年這部小說(shuō)的技巧性過(guò)重了?您現(xiàn)在怎么評(píng)價(jià)這部小說(shuō)?
韓少功:我很高興自己有過(guò)《爸爸爸》這樣的技術(shù)訓(xùn)練。好像是王安憶說(shuō)過(guò):一個(gè)作家畢生的寫(xiě)作就是造一個(gè)房子,里面有柱子,有梁,有墻,有門(mén)……《爸爸爸》有點(diǎn)寓言化,是這個(gè)房子里的某一扇門(mén)和某一個(gè)窗,不一定好,但不是其他東西可以替代的。
羊城晚報(bào):《日夜書(shū)》中有多個(gè)句子類(lèi)似于《百年孤獨(dú)》的開(kāi)頭。作為從上世紀(jì)80年代走來(lái)的作家,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加西亞·馬爾克斯,或者說(shuō)是拉美文學(xué)的影響?
韓少功:不是那樣吧?老馬的那種造句,是把三個(gè)時(shí)態(tài)壓縮在同一個(gè)句子,我想學(xué)也學(xué)不來(lái)。我只是用了一般的倒述句,很普通的。我當(dāng)然喜歡這位拉美作家,受了他多大的影響,自己也不知道。但他在中國(guó)的影響似乎被一些人說(shuō)過(guò)頭了,比如有一位國(guó)外的漢學(xué)家,以為中國(guó)文學(xué)里從來(lái)沒(méi)有神話,作家的夸張變形都是從拉美學(xué)的。我說(shuō)你讀一讀《山海經(jīng)》或《搜神記》再說(shuō)吧。我那篇《歸去來(lái)》,明明是莊周夢(mèng)蝶的結(jié)構(gòu),但有人也用來(lái)聯(lián)系老馬,實(shí)在沒(méi)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