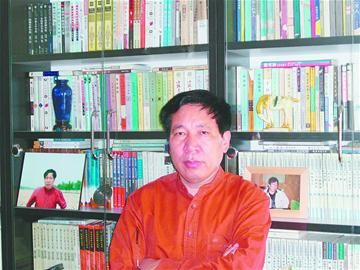

閻連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對文學現實的一次沖擊,多次獲得包括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在內的重要文學獎項,其作品被譯為日、韓、法、英、德、意大利、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十余種語言,在近二十個國家出版發行。最近,閻連科的散文《一個人的三條河》出版發行。小說家寫散文,一定是因為有話想說。在接受記者采訪過程中,閻連科發表了他對中國當代文壇很多作家的看法,認為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和莫言,不能相提并論。
“蔣方舟改變我對年輕作家的看法”
記者:去年您曾經和梁文道、蔣方舟一起做客騰訊的奧運節目“杯中話風云”,您的微博中也時常轉發蔣方舟的微博。我想知道作為一名老資格的作家,您怎么評價蔣方舟等80后90后新生代作家?
閻連科:我認為80后和90后這一代作家最終會取代上一代。蔣方舟的出現讓我改變了之前對新生代作家的看法。之前我覺得這一代作家很少關注社會,更加面向自己內心寫作。雖然有些西方偉大的作家也是面對自己內心的,中國的文學傳統還是更加講求文以載道。蔣方舟的寫作卻完全是關心他人的,她和之前的50后或者60后作家在這方面是相同的,有共同的文學目標。另外包括韓寒的雜文,張悅然的小說也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現在有些年輕的作家會向我推薦一些書,可以說80后和90后的年輕作家、批評家是我的另外一個書店。
記者:您最近的散文集《一個人的三條河》、《我與父輩》等受到了很多關注。近年來,小說家寫散文似乎也很時髦。比如最近張煒也出了散文年編。小說家為什么熱衷于寫散文了?
閻連科:首先,我認為并不是小說家開始寫散文了,而是散文的寫作伴隨大多數小說家一生。每個小說家都在寫散文,只是寫多寫少的問題。比如當代比較有名的作家韓少功、李銳、張煒、莫言等都在寫散文。當然,一個好的小說家不一定能寫出好的散文,雖然也有小說和散文都很好的,比如賈平凹和史鐵生。《我與父輩》之前,我的散文沒有被過多地關注,現在銷量和反響還不錯。寫散文對我來說是個很好的調整。小說是虛構的,里面的人物和事件離我身邊真實發生的還有一定距離,散文則和社會現實更近。小說和散文一虛一實,散文又能直抒胸臆,對作家來說是一種很好的補充。
記者:您如何評價您和同代人的寫作特點以及共同之處。
閻連科: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特點,我們這一代作家對社會的認識是和社會現實同步的。比如賈平凹近30年來的寫作就是和我們國家30年來整個發展相同步的。王安憶、莫言或許還寫了一些新中國成立之前遙遠的事,但是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越來越關注社會現實,關注現在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人在這樣的歷史現實中所處的窘境。這是因為我們這代人經歷的時代跨度太大,不僅僅是跨時代的人,也是跨文明跨制度的人。我們對國家和民族從哪里來,又將走向哪里,特別關心。80后和90后的寫作比較少關注社會和他人,大概正由于這代人不了解當下是從何處而來,他們生下來社會就是這個樣子了。
“因為《溫故1942》,我對劉震云的人格十分敬佩”
記者:您和劉震云同為河南人。他描寫大饑荒的作品《溫故1942》前段時間特別受關注,您亦有《四書》這樣相似題材的作品。您認為思考大饑荒對于這個民族的意義何在?
閻連科:《溫故1942》是劉震云所有小說作品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在他一生的寫作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有很多好的作品,我們讀了覺得好,但是不會對作家本人產生尊敬。但是讀完《溫故1942》之后,我們會對劉震云的人格產生敬仰之情。所有去寫饑荒、文革等苦難的作家都在試圖用他們的筆來恢復人們對民族的記憶,用個人的肩膀去承擔屬于整個民族的重量。無論《溫故1942》好與壞,這樣的作家都表達了他們對時代的思考。我希望中國的出版能更加開放,因為小說只是作家個人的藝術思考,文學作品只是為了作家的一點理想和一點藝術追求。
記者:您的散文對自己的解剖很深,比如完全不回避在父親病重時,產生的希望父親死去的閃念。您的寫作為何這樣大膽?
閻連科:我自己在寫作中,從來沒有想過“大膽”這兩個字。我覺得真實是一個藝術家最基本的要求,是最高也是最低的標準。一個作家能否正視自己,是對于作家本身的考驗。在我們的作家隊伍中,沒有特別重的宗教情懷,也沒有懺悔得特別徹底的作品。比如楊絳的《干校六記》、巴金的《隨想錄》,我們看了都覺得很高興,里面有對自己的反省和懺悔,但事實上這些作品懺悔得還不是那么徹底。我們可以面對別人,卻無法面對自己,但事實上通過反省自己,也能夠了解他人。
記者:您怎么看待小說的影視改編,蔣方舟說您語言“嗖嗖帶風得好”,是這種語言不容易改編為影視劇嗎?比如嚴歌苓,人們認為她的語言特別適合改編。
閻連科:小說的奇妙之處,在于沒有一種統一的標準。如果文學像數理化那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了,就沒有意思了。對于不同的作家,語言的地位不一樣。有的作家會認為情節最重要,有的會認為人物最重要。我覺得最好的語言是“個人化的語言”,有時候我找不到個人化的、不能和小說中人物很好結合的語言,我可能不會去寫。如果我的小說語言完成了前進和變化,這對于我來說是很大的成果。莫言的語言非常有特點,是非常個人化的語言,在他剛剛登上文壇的時候,比如《透明的紅蘿卜》等小說,給文壇帶來了很強硬的旋風。嚴歌苓的作品我沒怎么讀過,一部小說改編成影視作品談不上好與壞,但過度影視化并不是好事。如果一個作家的每一部小說都能改編成影視作品,那么就有可能偏離文學,和文學有些遠了。
“《泰囧》票房過10億是觀眾的喜劇、民族的悲劇”
記者:電影《一九四二》票房被《泰囧》攔腰截斷,中國的觀眾和讀者似乎都特別不喜歡苦難題材的作品。但是在希臘文化傳統中,又有悲劇凈化人心的說法,西方很多偉大的電影都是在講苦難的。您怎么看待當下中國觀眾和讀者主動回避苦難的現象?
閻連科:幾十年來我們的教育和意識改造在完成兩件事:一是忘記,二是不予思考。這兩點正成為一種文化深入人心。《泰囧》如果票房在5個億,我也不會覺得有什么奇怪,當它沖破了10個億,我認為這部電影就應該和《一九四二》沒有什么關系了。這樣的電影票房沖破10億,只能說明人們的忘記和不予思考完成得很徹底。我們也不能怪罪《泰囧》的制作人員,我們只是能看到“某種教育”的成功。這樣的票房差距,讓我們知道我們的民族和孩子們忘記民族歷史和選擇不予思考的情況到了一種什么樣的程度,也只有這樣,才會有更多的人去思考。對于觀眾,《泰囧》是一個喜劇,對于民族,這是一個悲劇。
記者:您在微博上也比較活躍,和您同時代的作家們,似乎不太擅長用微博,比如賈平凹。您如何看待這些新興的傳播方式?
閻連科:其實我比賈平凹還笨,不會用這些電子的設備,我現在也仍然用筆寫作。但是我身邊很多年輕人拉我進來,慢慢地就寫一些微博,也看和轉發別人的一些微博。對我來說,如果有時間就寫,沒有時間就不寫,沒有特別去經營微博,粉絲的多少我看也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微博讓我多了一個和社會聯系的渠道,多了一份作家看不到的報紙和雜志,它和我們能接觸到的報紙雜志等媒體是完全不一樣的。
記者:您覺得自己是一個有慈悲之心的作家嗎?
閻連科:我不認為我是。我的小說中有很多批判,多于同情和愛。但我在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覺得他對于人類的理解和愛是非常偉大的。我希望自己的怨氣能越來越少,更多地追求愛和同情。
“年輕作家應該認同經典村上春樹和莫言不能相提并論”
記者:您曾倡議80后和90后作家首先認同經典,為什么這樣說?
閻連科:我覺得一個作家對于某一經典的認識,是好或者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先要有一種認同。因為經典是經過時間檢驗的。比如魯迅,有那么多人罵他,我也批評過魯迅的愛太少,批判太多,但是他確實偉大。我們民族畢竟產生過李白、杜甫、白居易、曹雪芹以及沈從文這樣偉大的作家,只有從經典中汲取營養,才能夠寫出更好的作品來。好比現在問一個博士生的導師是誰,大致上可以了解他的文化背景。寫作雖然不能這樣絕對化,但是也有相通之處。有些年輕作家就認為村上春樹是唯一的偉大作家,我就難以和他們繼續交談下去。村上春樹我也讀,當然也很好,但是和之前日本的那些偉大作家比起來,村上春樹仍然是不可以和他們相提并論的。村上春樹也不能和莫言相提并論。他們的寫作方式、對文學的認識和追求是不一樣的,人生觀決定他們的藝術追求不同。總之可以罵魯迅,但是也請看完之后再罵吧。
記者:莫言獲獎,是去年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大事。作家木心曾經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全球范圍的中狀元,凡是中狀元就有運氣的成分在。也有人因此認為獲得諾獎不是多么難的事情,只需要自己的譯作被評委讀過,并且認為不錯。您怎么看待這種說法呢?
閻連科:諾獎有幸運的成分,但是特別要強調:一個作家能否被諾貝爾文學家關注,具有很大的必然性。首先,這個作家的作品要有很多人翻譯,但是這么多翻譯家為什么單獨翻譯這個作家的作品呢?我們先不去評論諾貝爾文學獎是否公平,但是作家的寫作、翻譯家的翻譯過程是非常艱辛的,我們都看到莫言獲獎的現在,但是在他獲獎之前那種寫作的艱苦,又有多少人看到呢?有人說翻譯家葛浩文對莫言作品的翻譯,是一種美化,但是如果沒有翻譯家,我們又怎么能讀到優秀的作品呢?我覺得一個作家,得不得獎不重要,重要的還是還原寫作本身,是否真正能寫出好作品,是否能最終被人們所接受。沈從文就曾經差一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因為他的確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所以得獎是有偶然性,但是被諾獎關注,是有必然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