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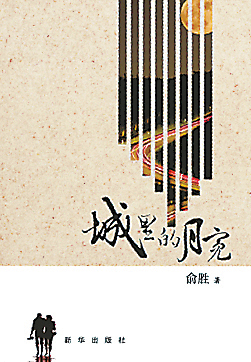
《城里的月亮》
俞勝 著
新華出版社出版
讀俞勝的文章也就在近一兩年的時間,那時大約被他“把小說寫得好看,把書評寫成散文”的話所吸引,想究竟他的小說“好看”在了哪里,而書評又是如何與散文掛上鉤的?以后就陸續在他的“指引”下看了一些文章,知道了他竟是個小說、散文、評論和報告文學的多面手。俞勝的散文文字優美,字里行間常常氤氳著一股山林雨霧般的氣息,清新、俊逸卻不脫智性的鋒芒;而書評卻并非真如我們印象中的“散文”,而是他向著“散文”的好讀看齊,力避文字的干澀枯燥之意。小說卻是好看的,印象最深的是何以他有這么徹骨的“肌膚”之痛,讓他處處把下層社會低微的生命體驗與精神困苦展現出來,表達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在“農村包圍城市,城市向鄉間隱退”的過程中,城市正與鄉村社會一起錯位,人們在迷茫、困頓、浮躁與焦灼中,陣痛并融合著。俞勝新近出版的小說集《城里的月亮》多數篇什突出集中反映了這一點。
拆遷問題是城市敘事中常見的題材,《水乳交融》講述了這么一個拆遷故事:小市民樊慧娜與丈夫甘四男日子過得緊巴巴的,房屋出租款成為一家的經濟支柱。但偏偏遭遇城市規劃必須拆遷,在拆與不拆的對峙與焦灼中,作為“小我”的樊慧娜在稍作掙扎后很快便與“大我”的權力機構妥協;不過,另一種精神層面的抗衡卻遠沒拆遷問題解決得快,那就是深深扎根在樊慧娜心中的城市人身份地位的優越感和生來自有的高高在上的精神潔癖。當發現租住在自己房屋的“外來農民工”李胖子在財富(錢比自己寬裕)、地位(丈夫成為他的打工仔)上勝過自己,甚至也和自己一樣擁有房產入住高檔小區之時,那一切看似固若金湯的優越感便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肉體的無所適從與精神的無所歸依在《水乳交融》中表現得十分到位。
與一般拆遷題材不同,俞勝沒有把重點放在“拆遷”題材通常表現官與民的對抗與妥協上,而是借助這個“象”把觸角伸向城市與鄉村兩種文化體系在城市化過程中文化的沖突與文化的和諧之上,表達一代人兩個群體之間微妙的心理糾葛與心靈感觸,這是一種時代的癥候,也是當前鄉村題材小說城市意象書寫的又一重要表現手法。可貴的是,俞勝對現實存在問題的揭示和追問,對卑微生命的描摹與刻畫,從來都不是帶著仇恨或鄙視的心態去控訴或詛咒,而是帶著深沉的責任感和同情心,去表現這些生命并呈現這個時代,讓我們在溫柔的觸痛中去看透生命的形態與時代的病象。事實上,俞勝筆下的人物大多都是生活于底層的小人物,無論《當我來到霞村的時候》的研究生“我”,還是《城里的月亮》的男主人公文生,抑或《老鄉》中的副處級干部姚小帥,他們本質上無一不以“外鄉人”的身份生活于這個“城市”之中。但就是他們這樣的小人物,有責任感、同情心,講究親情友誼,與通常的城市鋼筋水泥型的冷漠與疏離構成了強大的對比,這在一定程度上應和了我們賦予鄉村寧靜、質樸、敦厚的精神想象,是一種神性的“世外桃源”。只不過,在城市化的進程中,“物”日益占據中心,而“人”作為文化意義上的載體不斷邊緣化的當下,這種“世外桃源”究竟殘存幾何呢?
此外,俞勝《城里的月亮》還收錄有一些寓言體小說《人、狗、狼》《失落在街頭的小魚》《昆士郎博士和他的小螞蟻》等,頗有特色。與前述關注社會現實當下的小說相比,這些寓言體小說借助動物界的“它”眼光、“它”語氣,表達對幸福的真諦、個性自由、人盡其才等等社會哲理問題的反詰和思考。有意思的是,俞勝這組文章的主人公也是“它”界的弱者卑微形象,但它們卻不屈從命運,于是狗仗人勢竟也敢對狼怒吠,小螞蟻借人勢也敢在蚊王面前耀武揚威,但無一例外,它們在“人”面前又不得不奴顏婢膝處處小心地過著膽戰心驚的日子,一個身體兩副面孔在它們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當下社會的極度畸形狀態。
俞勝對自己的小說創作是有極清醒的認識的,他說他要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是以寫實的筆法直書社會,二要以寓言的手法反映現實。應該說,這“兩條腿”如今都已邁出十分堅實的步伐,也愿他在今后的小說道路上,越走越好,期待著他更多的好作品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