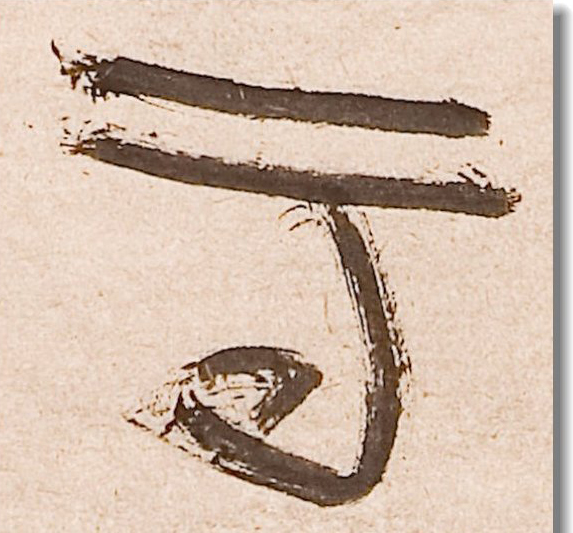篆書是中國傳統書法藝術中最為古老的一種書體,在中國書法發展史上,篆書自古以來就有著崇高而神圣的地位。清人錢泳以篆書為祖宗血脈,其一點一畫,皆有義理在。辟之讀書,大概篆書之于書法的意義就是儒家之六經,不由此入手,恐難得傳統之堂奧。然而在當代來說,能專攻篆書的人是不多的。這有幾個原因,一是篆書不易識別,同時需要文字學基礎,自非淺學者所易措手。其次,當代人好妍薄質,秀美一路的行草大興,而古厚樸茂的甲骨金文則少有人問津,前人說古質而今妍,時勢之必然。但是書法關乎文化,整個社會的文化以巧媚為能事,骨法澆漓,恐非幸事。
我以為,當代篆書的發展過程中,書家首先應該有文化自覺。換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那么對于搞篆書的書法家來說,首先要對篆書作為一種字體的發展歷程有充分的研究和把握,同時要認識到這種書體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意義。我認為漢字始終是中國文化建設的中心問題,關乎華夏文明的存廢與更新。中國文化的復興絕對繞不開漢字問題!篆書的發展不僅僅是藝術問題,更是文化問題,一定要從文化的高度認識篆書,篆書在當代的發展才有可能。
然而近百年來因為歐風美雨的洗滌,在藝術上,人們的觀念也開始混亂。就當代來說,很多人沒有把書法理解成一個綜合性的人格生態文化,而是僅僅將其理解成一種視覺藝術。在各種展覽和比賽中,大家也紛紛追求一種視覺效應。實際上,這是舍本求末的行為。而且其理論的立足點,也是西方的或者說西式的立場,沒有從中國文化的立場出發來思考這一問題,這不能不說是當代書法創作存在的最大問題之一。實際上,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與中國文化乃至民族的性格是聯系在一起的,中國人求中庸,求正大氣象,古人有大量這方面的論說,既以之論藝,更以之論人。顯然,險怪也好,巧媚也罷,在中國文化的認識論中,俱非正途,而古樸醇和,才是前賢追求的高境界,為藝如此,為人亦然。前人以學問有君子之學,有小人之學,也有妾婦之學,就是說世間的學問藝術,有的是正人君子治國平天下用的,有的卻僅僅是可以供婦女小孩娛樂用的。那么,這就涉及到作為一個書法家而言,自己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東西,是追求表面上的一點一劃或者視覺效果,還是追求其背后更遠大而深厚的文化。古人論書法,最重視人格修為,但是在當代書法的語境中,這一點卻被人們忽視了,這也可以說是當代書法的悲哀。
作為當代篆書創作來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追求視覺效果,忽略了篆書的文化屬性,對篆體篆法缺乏文字學源流的研究,而僅僅把古人的篆書當作一種造型資源來進行借鑒。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說,是有進步意義的,拓寬了書法創作思路,當然也有其片面性。那么我們就應該思考,當代篆書的發展,一方面總結研究前人的優秀學術、藝術成果,一方面也研究今人的審美,師古不泥古,化古為新,創造出具有鮮明時代特點,同時又是淵源有自的新時代的篆書藝術,這才應該是當代篆書發展一個正確的方向。因為我們不能脫離篆書深厚的傳統,也不能丟掉篆書自古以來的文化內涵,把篆書書法變成純粹的視覺藝術。同時,我們也不能在古人的藩籬中固步自封。這二者都不可取。潘天壽先生在探討中國畫發展的時候,曾經說過“不做洋奴隸,不做笨子孫”,這句話也值得我們當代每一個從事篆書藝術的書法家思考。
我認為當代篆書書法的發展,一定要追求“風骨”,前人以“生死剛正謂之骨”,風骨所包含的不僅是藝術上對力感的追求,更包括人格的力量。我們看歷代篆書大師的作品,從先民的甲骨金文一直到吳昌碩、齊白石,都體現出質樸深厚的藝術風貌,這種風貌背后一定是藝術家堂正浩然的心胸和人格。而在今天這樣一個商品經濟膨脹的社會來說,堂堂正正、頂天立地的高尚人格精神更是顯得珍貴。這種精神對一個國家而言稱之為國格,對一個民族而言則為民族氣節,而藝術雖然為“小道”,但關乎世道人心,故而我以為在藝術上有必要提倡一種正大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也就是文化的自覺。文化自覺,是篆書在當代有所發展,取得更加豐碩成果的一條必由之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