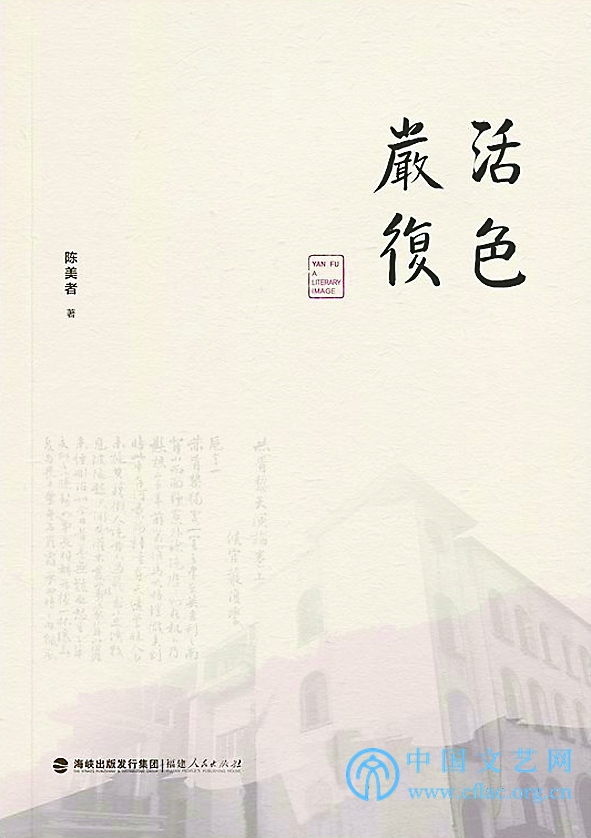《活色嚴復》
陳美者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
挫敗感折磨著嚴復一生,也穿過百年時光,折磨著那個試圖走進嚴復世界的人。
我不曾想,在美者筆下,嚴復竟會活得這般不如意。幾年前,我讀了一篇文章,了解過嚴復的科舉失敗史。但那也只是在一個具體方面說說嚴復的不走運,在世人眼中,實在無損于他的得意人生。嚴復是擠進了歷史圣殿的人,是有故居可以掛牌的人,是被成群結隊的游客瞻仰著的人,我們怎么可能想象,他這一生都被挫敗感纏繞著呢?據我所知,陳美者寫過一稿,不滿意,重寫一稿。我未曾見過第一稿,但我想,那里面的嚴復或許是另外一種生命風景吧?就像我們在傳記作品中讀過的許多歷史人物,幾乎都活在同一種人生楷模里——在風雨濘泥中砥礪奮進,最終開拓出一種昂揚勵志的生命境界。
不去想美者最初是如何寫嚴復的了。她最終呈現給我們的,確鑿無疑是一個無法擺脫挫敗感的嚴復。數次科考失利,許多人都知道,那是嚴復早年的恥辱和一生的心病。但是到了晚年,嚴復總該是有許多得意事可以顯擺的。當他在1918年回到故鄉陽歧,本該是達人榮歸故里的一副氣派。可是沒有,回顧一生,家累和國憂齊涌心頭,嚴復竟被淹沒在一種遺世情緒中。第一章《行香上書廟》,美者站在陽歧村這個地理坐標上寫嚴復的家累、國憂和科舉之殤,區區萬字寫盡了嚴復一生的不得意。但她沒有就此打住,到了第二章《風起馬頭江》,以馬尾船政為地理坐標寫嚴復在海軍、教育和翻譯三個領域的經歷,本可讓嚴復得意一些的,結果照樣是沮喪,用美者的話來說,就像是一手好牌被打爛了。這一番下來,似乎再無傷心事可寫了。但是到了第三章《夕照郎官巷》,美者站在一個名流云集的地理坐標上,卻聽出了嚴復內心憂傷的交響。大概沒有其他人會如美者這般,將嚴復的挫敗感寫到這份上了。
我隱隱覺得,倘若不是隔著遙遠時光,美者多半不會對嚴復產生興趣。大體來說,嚴復理性有余,卻少了點感性浪漫的生氣。他熱心于功名和時事,專注于實用之學,早期以進化論思想為時代演進推波助瀾,后期則求諸中式傳統,試圖力挽時代狂瀾。這樣的人,不能不說偉大,卻將現實世界擁抱得太緊,顯得有些無趣,不大可能引起美者的精神共鳴。我讀過美者的生活散文,大體印象如下:感覺至上,總能在日常生活的緊張間隙里發現詩性之光。這樣的美者,自然與過于理性的嚴復不太相稱,若在同一時空,兩個人對話起來,估計是要冷場的。我只能這么想,美者走進嚴復的世界,是一種誤會,也是一次例外。她只能以自己的眼光來打量嚴復,卻意外卸下了附加在嚴復身上的各種概念補丁,讓他重現出一點常人的活色來。她從最日常的飲食起居中看到了嚴復人生的真實。今天我們走進嚴復故居,多半只會遙想當年,嚴復是如何一等風流人物,又怎知他一生求個安穩居所而不得呢?杰出人物往往被各種概念打扮得光鮮亮麗,似乎真如中國人掛在口頭上的那句好話,萬事如意了。但是回到常人層面,總是十之八九不如意的。嚴復如此,美者或許也是這般。
當我讀完這部書稿,我告訴美者,我想從同情的角度來談談她的這次寫作。她似乎覺得不妥,問我,她有什么資格對一個歷史大人物表示同情呢?我未作解釋。我知道,今人理解的同情,是一種道德安撫,是優越者對弱勢者的憐憫和關懷。而我說的同情,不過是一種樸素眼光。它回到了初始語義,用來表示一個寫作者感知世界的基本態度和方法——人同此情。
今天我們把嚴復定位成一個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看到了他的不朽功業,然而回到當時,這些都只不過是嚴復無心插柳得來的,而他真正在意的,卻是求而不得的現實治用和現世功名。杜甫曾經心疼李白不得志,在詩中說道: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這話其實也適用在嚴復身上。嚴復之名,或許不負千秋萬歲,但是朝他身后看去,卻是一片寂寞的影子。這種寂寞跨越時空,百年之后凝結成心事絮語,回響在一個同情者的內心里。
在第二章,美者重點寫嚴復在海軍、教育和翻譯三個領域的經歷和成就。說起來,這部分內容是學術界研究得最透徹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美者再寫這些,真有點拾人牙慧了。我通讀書稿,就覺得這部分最為刻板和無趣,像科普工作者歷數一個名人的重大成就。但是寫嚴復,這些生命歷程又是無法越過的。美者其實面臨著一個巨大挑戰。好在行文到第三節,寫到嚴復的翻譯事業時,一筆神來,陡然翻轉了第二章的平庸局面。美者用了幾千字篇幅描述嚴復從事翻譯始末,使我們頓然明白,嚴復實則是因治世心切,卻又無從施展抱負,才投入這項事業中來的。而當政治理想最終破滅時,嚴復對自己的翻譯事業也就頗為懷疑,竟然把它說成是東抹西涂、妄竊名譽之舉了。簡單點說,挫敗感意外成就了嚴復的翻譯,而翻譯終究還是加深了嚴復的挫敗感。這可真是與眾不同的發現啊。倘若不是因為懷有一種同情心,美者寫到嚴復的翻譯,估計也只能人云亦云,重彈信、達、雅之類的老調了。
我讀美者寫老家往事的系列散文,總能看見那種在生命流沙中生成的詩性。但現在,美者需要面對的,是一個與其個人記憶沒有直接關聯的生命世界。當她帶著同情心走進這個世界,那個唯一真實的嚴復已消失,無數個局部真實的嚴復卻復活了。美者并沒有效仿多數傳記作品,以線性時間來安排寫作,從而避免走進唯一真實的死胡同。她以每個地標為想象起點,將嚴復個人史從線性時間中解放出來,重構一個具有立體時空感的生命世界,就如一幢層次繁復的建筑,外圍有多個入口標識,每進一個入口,我們都遇見一個嚴復,似曾相似,又不盡相同。有多少個地標被書寫,就有多少個嚴復在復活。每寫一個嚴復,都是一次同情的抵達。每一次抵達,都意味著踏進一個凝聚著歷史魂魄的地標,與一個熟悉的陌生人相遇。
同情是一種詩性智慧,隱含著非凡的想象和洞見。我由此判斷,美者是以真正的文學方法來寫嚴復的,自然不同于一般的傳記作品。文學批評家李長之寫過一本有關李白的小書,用了一個有趣的書名——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世人印象中,李白不是浪漫灑脫的嘛,何以在李長之筆下變成了痛苦的形象?這般理解一個詩人,經得起考證嗎?李長之在自序中說道,考證固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或許也是更重要的,則是同情——深入詩人內心世界,去體悟,去吟味。李長之是真正的批評家啊!他用純正的文學眼光,來看待文學中的關鍵問題,寫出來的文章自然也是讓人感到真切的。美者似無做個批評家的志向,走進嚴復的世界,或許也真是個意外,但是通過這次寫作,她恰好顯示了天生擁有的,那種被李長之認為更重要的文學眼光——同情。
一個人通過一次寫作,發現了一點自己,就是了不起的收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