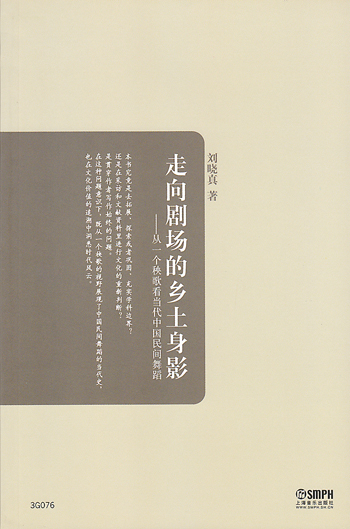
《走向劇場的鄉土身影》
劉曉真 著
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
對于強大的代表都市和精英文化的“學院派”以及舞臺化的“民族民間舞”的定名,鄉土民間舞仍是概念之外尷尬的徘徊者,只是被采之“風”和被表演的對象,其命運仍然是被“加工”與“提高”的無情切割與隨意組合,它所涵蓋的文化密碼隨著劇場競技與政治榮譽的角逐而逐漸消失,一代代積累的厚重的文化城墻將隨著價值觀的更換而瞬間坍塌。
劉曉真《走向劇場的鄉土身影——從一個秧歌看當代中國民間舞蹈》(以下簡稱《走向》)對以鼓子秧歌為代表的當代中國民間舞蹈風貌作了細致的歷史探究和發展論述。這本書在1949年的歷史節點上前后縱橫,并未耽于線性的考察與民間舞蹈“知識性”描摹與梳理,而是從一個較為宏觀的角度,對當代中國民間舞蹈在政治與文化格局變化中的生存境遇選擇,在經濟沖擊與信仰衰落之中的身體變化,在面對非遺時形態“新”與“舊”的價值迷茫做了深入的思考和理性的闡述。
長期以來,舞界學人多將民間舞從“原生形態”的自足保守到“教學形態”身體規訓的元素提取依據,最終在“劇場形態”中再次將身體進行精英文化的洗滌與過濾,形成“提取再造”的身體語言。但是,在中國當代民間舞蹈的發展中存在這樣的特例:由于農耕社會長期的文化特質和歷史積淀,中國的鄉土藝術在走向當代的進程中是在“劇場”和“鄉土”的雙重行走中完成互動與吸納,并在新的形式中開始雅與俗、精英與大眾、大傳統與小傳統的文化循環。《走向》一書的出發點和意義即在于此——既有自由的思想銳氣,也激發讀者的理性思辨與學理的探索空間。之所以選擇“鼓子秧歌”為個案,是因為在時代的浪潮中,鼓子秧歌一方面保持著地方性經驗所構成的鮮明特色,另一方面也“處于一個似乎更為先知先覺的優勢位置,與舞蹈專業院校、各種國家儀典、活動的緊密關系,使它的發展出現了并行不悖、穿插交疊的兩條線索,一方面我們看到鼓子秧歌在山東當地延續傳統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它積極參與國家文化形象建設的現代步伐。”如此,山東鼓子秧歌的現實給我們打開了中國民間舞在當代劇場演藝、國家意志以及民間自發表演中的種種生存現狀和價值取向。
猶如一把雙刃劍,鼓子秧歌在獲得政治和經濟認同的同時,對政治榮譽和經濟價值的過度追求,使它漸漸脫離“土味”。作者劉曉真自2001年起對山東商河縣、濟陽縣、惠民縣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并在散落的資料中爬梳剔抉,整理歸納,對1955年至2003年商河鼓子秧歌參加的國家、省市級重要演出進行了統計,在肯定了鼓子秧歌參與新的國家敘事話語的同時,也指出這樣的問題:第一,由于名聲所累,最具代表性的鼓子秧歌手們頻頻參加由各地各級政府組織的演出,到了真正的年節“跑十五”時熱情卻在下降,傳統的串村儀式簡化或取消,民俗意義在“秧歌搭臺,經濟唱戲”的行政操作手段中隱退。第二,在身份的意識上,由于商河政府的資金投入,民間藝人“把鼓子秧歌作為可以賺錢的營生”,認為比“民間藝人”的身份要“實惠得多”,秧歌的熱情由祭祖、自娛轉化為對經濟的自覺。第三,由于引進比賽機制,介于“博士”和“二老藝人”之間的文化館員成為鼓子秧歌實際的指導和加工者。這些長期工作在一線的文化館員,以自己的文化理解和審美感悟對鼓子秧歌進行的創新或提高,使鼓子秧歌的發展獲得另一種機制的保障,但其中的模式也值得商榷與思考。這些,無疑也是當下“原生形態”民間舞“走向”的癥結所在。這種對民間舞蹈在國家主線之外發展的擔憂和思慮,也是一個長期行走于田野和劇場之間的青年學者的學術自覺。
對于強大的代表都市和精英文化的“學院派”以及舞臺化的“民族民間舞”的定名,鄉土民間舞仍是概念之外尷尬的徘徊者,只是被采之“風”和被表演的對象,其命運仍然是被“加工”與“提高”的無情切割與隨意組合,它所涵蓋的文化密碼隨著劇場競技與政治榮譽的角逐而逐漸消失,一代代積累的厚重的文化城墻將隨著價值觀的更換而瞬間坍塌。
或許正是這些多元生存的形式,中國民間舞的文化自覺和舞蹈自律才以“非遺”的形式迫在眉睫地提到日程上來。這里的“舞蹈”主要成分即“鄉土”民間舞,包括它們身體的“觀念表達”、“表現方式”、“技能”及與之相關的服飾道具和“文化場所”。失去了這一真實,那些變換的身影就會成為魂不附體的真正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