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低成本電影如何在消費市場保持生存空間
中低成本的中國電影難以在中國消費市場走紅,走向國際電影市場更是征途漫漫,中國電影人需要反思,為什么以關注社會底層人物生命現狀為主、敘事手法樸實見長的伊朗電影,能長期在國際影壇占有一席之地,描寫當代中國普通百姓現實存在的電影卻難以走出國門?新觀眾的引出,新市場的形成,需要中國電影人認真研究變化中的新形勢,探索中國電影新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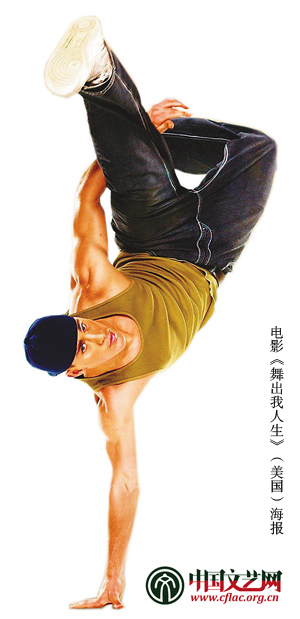 2013年,我國故事片產量638部;全國總票房217.69億元,同比增長27.51%,其中國產片127.67億元,同比增長54.32%,占比58.65%。這些數字令人鼓舞,又不容過分樂觀。因為中國對美國電影仍實行配額制,如果進口片市場完全放開,形勢可能逆轉,另一方面,中國電影打開歐美市場仍任重道遠。當下中國電影人,特別是電影業的新生代,面對國內外電影市場的挑戰,如何應對好萊塢攻勢?如何堅守電影藝術創作底線?電影作品如何適應青少年觀眾需求?中低成本電影如何在消費市場保持生存空間?這些問題令我們深思。
2013年,我國故事片產量638部;全國總票房217.69億元,同比增長27.51%,其中國產片127.67億元,同比增長54.32%,占比58.65%。這些數字令人鼓舞,又不容過分樂觀。因為中國對美國電影仍實行配額制,如果進口片市場完全放開,形勢可能逆轉,另一方面,中國電影打開歐美市場仍任重道遠。當下中國電影人,特別是電影業的新生代,面對國內外電影市場的挑戰,如何應對好萊塢攻勢?如何堅守電影藝術創作底線?電影作品如何適應青少年觀眾需求?中低成本電影如何在消費市場保持生存空間?這些問題令我們深思。
中低成本電影首先要講好中國故事
2012年,一部成本不高的美國電影《烏云背后的幸福線》風靡世界影壇,該片獲2012年第37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最高獎項——人民選擇獎,并在第85屆奧斯卡金像獎獲得8項提名,最終獲得最佳女演員獎。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位高中歷史教師,他因精神疾病住院4年,妻子離他而去。這位中年人生性樂觀,出院后仍不放棄人生追求,最終收獲了新的愛情。眾所周知,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獲獎作品評選主旨是面向市場,從來不設專業人士評獎,而是由觀眾投票評選最佳影片,名為“人民選擇獎”。這部影片,連同此前獲獎的《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以及在世界各大電影節獲獎無數的伊朗電影《一次別離》等,都是中低成本電影,這些影片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講述普通人的情感與生存狀態,故事動人,感情真摯,能觸動人的心靈深處。
中國近年來也出品了一些中低成本的優質電影,比如《鋼的琴》,故事好,音樂好,表演精湛,但因為資金捉襟見肘,后期宣傳投入甚少,導致市場反響冷清。
中低成本的中國電影難以在中國消費市場走紅,走向國際電影市場更是征途漫漫,在這方面,中國電影人需要反思,為什么以關注社會底層人物生命現狀為主、敘事手法樸實見長的伊朗電影,能長期在國際影壇占有一席之地,描寫當代中國普通百姓現實存在的電影卻難以走出國門?究其所因,顯而易見的是我們缺少好劇本成就的好故事。
中國一些名導之作熱衷于描寫人性的陰暗,扭曲的情欲,價值觀的淪喪,信念的缺失。特別是一些喜劇片,內容怪誕,表演夸張,噱頭低俗,雖然在中國走紅,卻在歐美遭遇惡評,由此,值得中國影人精心思量一下個人的藝術操守和美學傾向。
如何能講好中國故事,我們不妨聽一聽青年導演寧浩近期的一段訪談之言:人性是由動物性和社會性兩部分構成的。動物性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人的思維和行為中的利己主義;社會性則更多地表現為自我犧牲和奉獻精神,或者說利他主義,社會性是人在成長中不斷獲得啟蒙和陶冶才能得到的。寧浩說,他的作品是想要表現人之所以為人應具有的社會性追求,通過曲折故事中的人與事對人性深度揭示,讓觀眾感受真與善融合至美的感召,從而向社會傳遞更多的正能量,傳遞出對于善良人性的呼喚和尊重。
呼喚和尊重善良人性,應當是中國當代題材電影走向世界的重要創作取向之一。我們的電影故事,應該以此切入,講好“人之初,性本善”的樸素道理。盡管《唐山大地震》《金陵十三釵》《1942》等大片已進行過嘗試和示范,但還遠遠不夠。我們想一想,每年央視感動中國年度人物頒獎典禮現場直播的內容中,哪個人背后沒有一段催人奮進、感人淚下的故事,為什么這些感人的故事拍成電影就無人喝彩,是我們電影人的問題,是故事本身的問題,還是大環境核心價值追求的問題,這值得我們深思。我們應該淡化宏大敘事的套路,探索如何架構組合新的電影語言來講述感動當代中國的好故事。像美國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拯救大兵瑞恩》《幫助》等,均源自真人真事,卻又不拘泥于真人真事,以藝術化和電影化思維的再創作,深入主人公內心世界的解讀,借助人物內心外化的行為動作,以為他人奮不顧身、真誠善良、生動感人的正面形象,強化作品藝術表現力與思想感染力,提升民族整體氣質,進而作用于人類文明進程的推進。
中國電影必須重視市場消費者的心理需求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城鎮化步伐的加快和城市人口的迅速遞增,中國電影市場正迎來一個快速發展期。一方面,一、二線城市的電影院隨著城市綜合體滿城開花而落戶許多社區,中小城市也開始涌現新型電影院;另一方面,到影院觀看電影成為中國平民受眾相對而言的“高消費”文化,動輒幾十元的票價將城市里許多低收入者、中老年人擋在門外,更不要說外來農民工及其子女。于是,中國城市出現一道奇特風景,中老年婦女大跳廣場舞,年輕人(多是白領階層和大學生)則涌進電影院“談情說愛”,電視機前看電影則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無奈的選擇。面對當下電影觀眾群的演變分化,市場需求十分明顯,電影必須是大制作、大場面、大明星對受眾才有號召力。至于電影類型,好萊塢的“俠”(蝙蝠俠、蜘蛛俠、鋼鐵俠)、“幻”(哈里波特、指環王、暮光之城)系列,最能抓住年輕人的眼球。這些系列大片共有的特征是:場景奇幻,飛天跨海,加上3D效果,在電腦上觀看難以過癮,必須到電影院享受大銀幕、縱深空間和環繞立體聲的視聽盛宴。到電影院看電影成為都市年輕人的社交時尚文化,其休閑娛樂功能被疊加放大。另一方面,作為城市、鄉村的普通勞動者,誰愿意掏幾十元錢到電影院接受說教式的再教育?誰愿意在勞累之后還到電影院看窮苦人家凄凄慘慘、哭哭啼啼、生不如死?因此,悲劇讓位于喜劇、思考讓位于娛樂、審美讓位于審丑、雅文化讓位于俗文化已不足為怪,這就是中國電影市場的現實,或者說當下電影受眾的趨向選擇。
新觀眾的引出,新市場的形成,需要中國電影人認真研究變化中的新形勢,探索中國電影新出路。中國中小成本電影的制作者多為電影新生代,盡管他們融資能力有限,請不起大明星和高級制作團隊,自然也無力于大場面、大特技所需資金的投入,但他們卻能把握同齡觀眾的電影文化心理需求,包括同齡人的興趣點和興奮點。郭敬明導演的《小時代》就是一個明證,他與年輕團隊的一把火,就能點燃2013年7月舉國的電影市場。雖然僅是一部面向年輕人的娛樂片,但對中國影人卻是個提醒。中國導演不能只滿足于個人狹隘的藝術空間追求,只拍攝表現個人藝術情趣的作品,而要面對受眾,思考他們的心理指向,尊重他們的觀影意愿,將藝術的審美功能和娛樂功能自然而貼切地融合于作品,讓電影創作意識跟上市場審美主流群體的心理節奏,滿足不同消費群體的觀影選擇。
以青少年題材電影為例,從時尚文化、背包旅游、野外生存,到校園愛情、求職奮斗、成家立業,從童話、科幻、奇幻,到驚悚、災難、驅鬼,從愛護動物、保護生態,到禁毒、預防艾滋,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題材,哪里有青少年,哪里就有他們的故事,關鍵在于我們如何貼近他們,如何寫他們,如何引起他們的關注和喜歡,如何提升他們的審美取向,如何引導他們信仰的健康方向和面對現實的樂觀態度。
更新電影創作觀念與尊重受眾期待
有專家指出,文化市場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電影是文化領域中市場化程度和產業化水平較高的行業之一。作為中國電影人,需要完成從電影藝術工作者到電影產品制作者的觀念轉變,我們的創作要走出傳統思維模式,拋棄陳舊封閉的藝術表現手段,以視聽語言創新、發現造就新一代優秀演員,制作技術精良引領電影產業的現代化進程,開拓國內國際市場。
就以制作電影的科幻、奇幻場面為例。不少中國電影人一提起科幻片,就搖頭感嘆中國缺乏數字特效人才,做不出那些宇航探險、星球大戰的場面。人們不禁要問,既然中國能造出宇宙飛船探月,為何就做不出科幻電影場面?是缺人才,還是缺創意?中國導演對現代科技本身特別是數字技術發展趨勢有多少了解?對其有多少興趣?又如動畫片,美國創制的電影《花木蘭》《功夫熊貓》成功講述了中國古代與現代的故事,其實美國有好多動畫片是在中國繪制加工的,成都就有幾個團隊曾參與此類電影的國際合作,可見中國并不缺少動畫人才,而是缺少領軍人物,缺少與電影投資集團的產銷對接。
科幻片、奇幻片、童話片、動畫片并非都需要大投入,一些清新小制作也能撬動電影國際市場。例如,法國電影《天使愛美麗》,就有一些奇幻場景,其嶄新的銀幕呈現,既豐富了影片畫面新視覺效果和人物立體形象的生成,又非常貼近主題,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法國動畫片《瘋狂約會美麗都》,不以恢宏場面取勝,而是追求在有限的空間里,著力于借助人物交織關系的精心建構,講述一段感人的故事,影片的音樂旋律優美動聽,堪稱一大亮點。
再如現代歌舞片,美國的歌舞片多以青少年為主角,深受年輕觀眾喜愛。如《歌舞青春》就連拍三集,捧紅了男女主角埃夫隆和哈金斯,成為新一代青春偶像。《舞出我人生》已連拍四集,至今國際受眾熱度不減。我們可以從這些影片的市場回饋獲得啟示,破除對科幻片、奇幻片的畏懼,以及對歌舞片的回避,努力創新,讓中國電影能夠呈現多品種、多元化、多類型的百花齊放局面,充滿活力和引力地滿足市場需求。
(編輯:曉婧)

